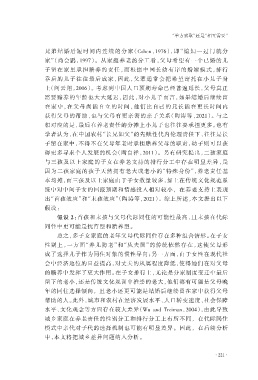Page 228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228
“单方索取”还是“相互需要”
兄弟结婚后短时间内连续的分家(Cohen,1976),即“媳妇 一 过 门 就 分
家”(尚会鹏,1997)。 从家庭养老的分工看,父母希望有一个已婚的儿
子留在家里承担赡养的责任,而根据中国长幼有序的婚嫁模式,排行
靠后的儿子往往最后成家,因此,父辈通常会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
上(阎云翔,2006)。 考虑到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已经普遍延长,父母真正
需要赡养的年龄也大大延迟,因此,对小儿子而言,如果结婚后继续留
在家中,在父母尚能自立的时间,他们比自己的兄长能在更长时间内
获得父母的帮助,也与父母有更亲密的亲子关系(陶涛等,2021)。 与之
相对应的是,最后在养老责任的分摊上小儿子也往往要承担更多。也有
学者认为,在中国农村“长兄如父”的先赋性代内伦理责任下,往往是长
子留在家中,不得不在父母年老时承担赡养父母的职责,幼子则可以获
得更多寻求个人发展的机会(陶自祥,2011)。 另有研究提出,二孩家庭
与三孩及以上家庭的子女在养老支持的排行分工中存在明显差异,是
因为二孩家庭的孩子天然拥有老大或老小的“特殊身份”,养老责任基
本均摊,而三孩及以上家庭由于子女数量较多,加上在传统文化规范系
统中对中间子女的回报预期和情感投入相对较小, 在养老支持上表现
出“首孩效应”和“末孩效应”(陶涛等,2021)。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2:首孩和末孩与父母代际同住的可能性最高,且末孩在代际
同住中更可能是抚育型和赡养型。
总之,多子女家庭的老年父母代际同住存在多种组合情形。在子女
性别上,一方面“养儿防老”和“从夫居”的传统依然存在,这使父母形
成了选择儿子作为同住对象的惯性导向;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在现代社
会中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对丈夫的从属程度降低,使得她们在对父母
的赡养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在子女排行上,无论是分家制度变迁中最后
留下的老小,还是传统文化规训中推崇的老大,他们都有可能是父母晚
年的同住选择倾向, 且老小还更可能是结婚后继续留在家中获得父母
帮助的人。此外,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转变速度、社会保障
水平、文化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Wu and Treiman,2004),由此导致
城乡家庭在养老责任的性别分工和排行分工上有所不同, 在代际同住
模式中亲代对子代的选择机制也可能有明显差异。 因此, 在后续分析
中,本文将把城乡差异问题纳入分析。
·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