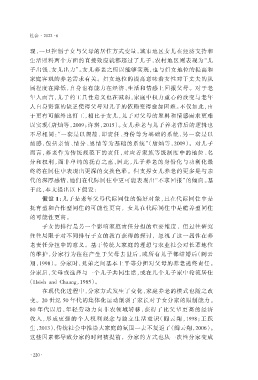Page 227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227
社会·2022·6
现,一旦控制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变量,城市地区女儿在经济支持和
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就都超过了儿子,农村地区则表现为“儿
子出钱、女儿出力”。女儿养老之所以能够实现,也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
家庭客观的养老需求有关。 妇女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女性对于丈夫的从
属程度在降低,自身也有能力在经济、生活和情感上回报父母。 对于老
年人而言,儿子的工具性意义也在减弱,家庭中权力重心的改变与老年
人自身资源的缺乏使得父母对儿子的依赖变得愈加困难。 不仅如此,由
于更有可能外出打工,相比于女儿,儿子对父母的照料和情感需求更难
以实现(唐灿等,2009;许琪,2015)。 女儿养老与儿子养老背后的逻辑也
不尽相同:“一套是以规范,即责任、身份等为基础的系统,另一套是以
情感,包括亲情、情分、恩情等为基础的系统”(唐灿等,2009)。 对儿子
而言,养老作为传统规范下的责任,对应着家族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名
分和权利,而非单纯的抚育之惠,因此,儿子养老的身份化与功利化最
终将在同住中表现出更深的交换色彩。 但支撑女儿养老的更多是与亲
代的深厚感情,她们在代际同住中更可能表现出“不求回报”的倾向。基
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儿子是老年父母代际同住的偏好对象,且在代际同住中是
抚育型和合作型同住的可能性更高, 女儿在代际同住中是赡养型同住
的可能性更高。
子女的排行是另一个影响家庭责任分担的重要维度, 但过往研究
往往局限于对不同排行子女的教育获得的探讨, 忽视了这一属性在养
老责任分担中的意义。 基于传统大家庭的理想与农业社会对长辈地位
的维护,分家行为往往产生于父母去世后,或所有儿子都结婚后(阎云
翔,1998)。 分家时,兄弟之间基本上平等分担对父母的养老送终责任。
分家后,父母或选择与一个儿子共同生活,或在几个儿子家中轮流居住
( Hsieh and Chuang,1985)。
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家方式发生了变化,家庭养老的模式也随之改
变。 20 世纪 50 年代的集体化运动削弱了家长对子女分家的限制能力。
80 年代以后,年轻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获得了比父辈更高的经济
收入,形成更强的个人权利观念与独立生 活 意识(阎 云 翔 ,1998;王 跃
生,2013),传统社会中推崇大家庭的氛围一去不复返了(阎云翔,2006)。
这些因素都导致分家的时间被提前, 分家的方式也从一次性分家变成
·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