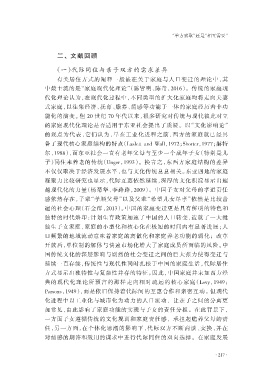Page 224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224
“单方索取”还是“相互需要”
二、 文献回顾
(一)代际同住与亲子双方的需求差异
有关居住方式的阐释一般嵌在关于家庭与人口变迁的理论中,其
中最主流的是“家庭现代化理论”(陈皆明、陈奇,2016)。 传统的家庭现
代化理论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扩大化家庭均将走向夫妻
式家庭,以往集经济、抚育、赡养、情感等功能于一体的家庭经历着非功
能化的演变。 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很多研究对传统与现代彼此对立
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是否适用于东亚社会提出了质疑。 以“文化影响论”
的观点为代表,它们认为,早在工业化进程之前,西方的家庭就已经具
备了现代核心家庭结构的特点( Laslett and Wall,1972;Shorter,1977;赫特
尔,1988),而东亚社会一直有老年父母与至少一个成年子女(特别是儿
子)同住来养老的传统( Unger,1993)。 换言之,东西方家庭结构的差异
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也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东亚四地的家庭
凝聚力比较研究也显示,代际互惠依然延续,深厚的文化积淀显示出超
越现代化的力量(杨菊华、李路路,2009)。 中国子女对父母的孝道责任
感依然存在,子辈“孝顺父母”以及父辈“希望儿女尽孝”依然是比较普
遍的社会心理(石金群,2013)。 中国的家庭变迁更是具有鲜明的特色和
独特的时代烙印: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造就了一大批
独生子女家庭,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显著进展;人
口频繁的地域流动意味着家庭的离散化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改革
开放后,单位制的解体与快速市场化增大了家庭成员所面临的风险。 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得变迁与
延续一直存续,传统性与现代性同时扎根于中国的家庭生活,代际居住
方式显示出独特性与复杂性并存的特征。 因此,中国家庭并未如西方经
典的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相对疏远的核心家庭(Levy,1949;
Parsons,1949),而是依旧保持着代际间的互惠合作和亲密互动。 但现代
化进程中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动力的人口流动, 让亲子之间的分离更
加常见,由此影响了家庭功能的实现与子女的责任分担。 在此背景下,
一方面子女遵循传统的文化规训和家庭责任感, 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
任,另一方面,在个体化思潮的影响下,代际双方不断商谈、交换,并在
对情感的期许和效用的谋求中进行代际同住的双向选择。 在家庭发展
·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