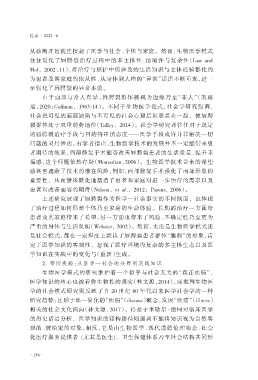Page 143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143
社会·2022·6
从诊断开始就连接起了医学与社会、个体与家庭。 然而,生物医学模式
往往简化了唇腭裂治疗过程中的多主体性、情境性与复杂性(Law and
Mol, 2002:11),将治疗与照护中所涉及的生活知识与主体经验都化约
为患者及其家庭的依从性,从身体到人格的“异常”话语不断重现,进一
步强化了唇腭裂的异常本质。
由于面部与常人有异,唇腭裂群体被视为边缘乃至“非人”(刘瑶
瑶,2020;Goffman, 1963:14)。 不同于生物医学范式,社会学研究强调,
社会把可见的面部缺陷与不可见的社会心理后果联系在一起, 使唇腭
裂群体处于双重弱势地位( Talley, 2014)。 社会学研究者往往对于既定
的唇腭裂治疗手段与目的持审慎态度———医学手段或许并非解决一切
问题的灵丹妙药。 有学者指出,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患
者期待的效果,面部修复手术能否改善唇腭裂患者的生活质量、提升幸
福感,这个问题依然存疑( Mouradian,2006)。 生物医学技术带来的希望
感甚至遮蔽了技术的潜在风险,例如,面部修复手术强化了面部形象的
重要性, 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患者和家庭对进一步治疗的需求以及
患者对改善面容的期待( Nelson, et al., 2012; Parens, 2006)。
上述研究展现了唇腭裂作为医学—社会事实的不同侧面, 也体现
了治疗过程如何形塑个体乃至家庭的生命体验。 长期的治疗一方面给
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希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风险、不确定性乃至更为
严重的身体与生活负担(Webster, 2002)。 然而,无论是生物医学模式还
是社会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唇腭裂患者群体“脆弱”的形象,肯
定了医学知识的客观性, 忽视了医疗环境内复杂的多主体生态以及医
学知识在实践中的变化与(重新)生成。
2. 带回疾病:从医学—社会的分野到实践知识
生物医学模式的研究维护着一个似乎与社会无关的“真正疾病”,
医学知识的核心也被看作生物性的现实(林文源,2014)。 而批判生物医
学的社会模式研究则反映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医学社会学的一种
研究趋势:区别于单一简化的“疾病”(disease)概念,发展“疾痛”(illness)
相关的社会文化面向(林文源,2017)。 得益于米歇尔·福柯对临床医学
的历史话语分析, 医学知识的建构路径则强调不能将知识视为自然客
观的、被给定的对象,相反,它是由生物医学、现代道德伦理观念、社会
化医疗服务提供者 (尤其是医生)、 卫生保健体系乃至社会结构共同形
·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