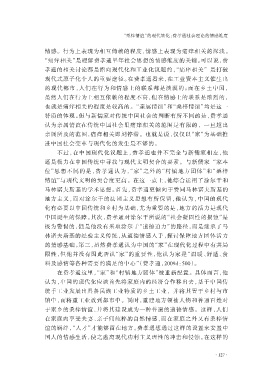Page 134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134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情感。 行为上表现为相互倚赖的程度,情感上表现为痛痒相关的深浅。
“痛痒相关”是理解费孝通早年社会思想的情感维度的关键。可以说,费
孝通的相关讨论都是指向现代化和工业化议题的,“痛痒相关” 是打破
现代式原子化个人的重要途径。 在费孝通看来,在工业资本主义催生出
的现代都市,人们在行为和情感上的联系都是淡漠的;而在乡土中国,
虽然人们在行为上相互依赖的程度不高,但在情感上的联系是浓烈的,
也就是痛痒相关的程度是较高的。“亲属情谊”和“桑梓情谊”均是这一
特质的体现。 但与新儒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判断有所不同的是,费孝通
认为亲属情谊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痛痒相关的范围是有限的, 一旦超出
亲属所及的范围,痛痒相关即刻停滞。 也就是说,仅仅以“家”为基础推
进中国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发生是不够的。
不过,在中国现代化议题上,费孝通也并不完全与新儒家相左,他
还是极力在中国传统中寻找与现代文明契合的要素。 与新儒家“家本
位”思想不同的是,费孝通认为,“家”之外的“村镇地方团体”和“桑梓
情谊”与现代文明的契合度更高。 在这一点上,他综合运用了涂尔干和
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思想。 首先,费孝通更倾向于赞同马林诺夫斯基的
地方主义,而对涂尔干的法团主义思想有所保留,他认为,中国的现代
化有必要以中国传统和乡村为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地方的活力是现代
中国诞生的保障。其次,费孝通对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凝固性的损蚀”是
极为警惕的,但是他没有采取涂尔干“道德迫力”的路径,而是继承了马
林诺夫斯基的经验主义传统,从道德情感入手,探讨保障地方团体活力
的情感基础。第三,虽然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其局
限性,但他并没有因此否认“家”的重要性,他认为家是“温暖、舒适、食
料及感情等各种需要的满足的中心”(费孝通,2009d:500)。
在费孝通这里,“家”和“村镇地方团体”被重新配置。 具体而言,他
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首先将家庭内的经济合作移出去,基于中国传
统手工业发展出具备民族工业特质的乡土工业, 并将其置于乡村与市
镇中,而将重工业放到都市中。 同时,重建地方领袖人物和普通百姓对
于家乡的桑梓情谊,并将其建设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感。 这样,人们
在家庭内享受夫妻、亲子间纯粹的自然情感,而在家庭之外又有桑梓情
谊的羁绊,“人才”才能够留在地方。费孝通想通过这样的设置来安置中
国人的情感生活,使之逃离现代功利主义理性的冲击和侵蚀。 在这样的
·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