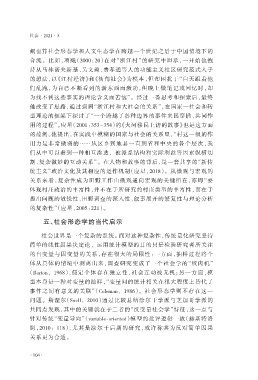Page 111 - 《社会》2021年第5期
P. 111
社会·2021·5
概也算社会形态学和人文生态学在跨越一个世纪之后于中国情境下的
合流。 比如,项飚(2000:20)在对“浙江村”的研究中坦承,一开始他抱
持从马林诺夫斯基、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范式入手
的想法,以《江村经济》和《街角社会》为模本,但却困扰于“白天跟着他
们乱跑,为自己不断看到的新东西而激动,但晚上做笔记或回忆时,却
为找不到这些事实的理论含义而苦恼”。 经过一番思考和探索后,最终
他改变了思路,通过强调“浙江村和大社会的关系”,在国家—社会和转
型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一个跨越了各种边界的事件来回穿插、共同作
用的过程”。应星( 2001:353-354)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也是这方面
的范例。他提出,在实践中模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里,“村这一级的作
用力是非常微弱的……从区乡到地县一直到省和中央的各个层次,我
们从中可以看到一种相互渗透, 被派系结构和实际利益等因素纵横切
割、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 在人物和故事的背后,是一套共享的“新传
统主义”政治文化及其相应的运作机制(应星,2018)。 从微观与宏观的
关系来看,复杂性成为田野工作由微观通向宏观的关键所在,亦即“要
体现村庄政治的丰富性,并不在于所研究的村庄类型的丰富性,而在于
提出问题的敏锐性、田野调查的深入性、叙事展开的繁复性与理论分析
的复杂性”(应星,2005:221)。
五、社会形态学的当代启示
社会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面对这种复杂性,传统量化研究坚持
简单的线性因果决定论, 运用统计模型的目的只是检验研究者所关注
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抽样过程将个
体从具体的情境中剥离出来,调查研究变成了一个社会学的“绞肉机”
(Barton, 1968),假定个体存在独立性,社会互动被无视;另一方面,模
型本身是一种对变量的抽样,“变量间的统计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
事件之间有意义的关联”(Coleman, 1986)。 社会形态学则不存在这一
问题。 斯涅尔(Snell, 2010)通过比较总结涂尔干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
共同点发现,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二者的“反变量社会学”特征,这一点与
针对传统“变量导向”(variable鄄oriented)模型的批评逻辑一致(赫斯特洛
姆,2010: 118),尤其是涂尔干后期的研究,或许称其为反对简单因果
关系更为合适。
·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