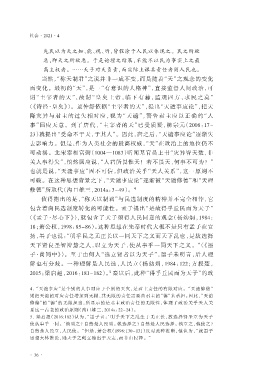Page 43 - 《社会》2021年第4期
P. 43
社会·2021·4
先民以为天之知、能、视、听,皆假涂于人民以体现之。 民之所欲
恶,即天之所欲恶。 于是论理之结果,不能不以民为事实上之最
高主权者。 ……天子对天负责,而实际上课其责任者则人民也。
当然,“称天制君”之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天”之观念的变化
而变化。 最初的“天”,是一“有意识的人格神”,直接监督人间政治,可
谓“主 宰 者 的 天 ”, 故 谓“皇 矣 上 帝 , 临 下 有 赫 , 监 观 四 方 , 求 民 之 莫 ”
(《诗经·皇矣》)。 董仲舒依据“主宰者的天”,提出“天谴事应论”,把天
降 灾 异 与 君 主 的 过 失相 对 应 ,视 为“天 谴 ”,警 告 君 主 应 以 正 确 的“人
事”回应天意。 到了唐代,“主宰者的天”已受质疑,柳宗元( 2008:17-
23)就提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因此,唐之后,“天谴事应论”逐渐失
去影响力。 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权威,“天”在政治上的地位仍不
可动摇。 北宋宰相富弼( 1004—1083)听闻某官员上书“灾异皆天数,非
关人事得失”,愤然回应说,“人君所畏惟天! 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 ”
也就是说,“天谴事应”固不可信,但政治关乎“天人关系”,这一原则不
可破。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天谴事应论”逐渐被“天谴修德”和“天理
修德”所取代(沟口雄三,2014a:3-49)。 4
值得指出的是,“称天以制君”与民选制度的精神并不完全相悖,它
包含着向民选制度转化的可能性。 孟子提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孟子·尽心下》),就包含了天子须得人民同意的观念(杨幼炯,1984:
18;萧公权,1998:85-86)。这种思想在先秦时代大概不是只有孟子在宣
扬,墨子也说:“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
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以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墨
子·尚同中》)。 至于由何人“选立贤者以为天子”,墨子未明言,后人理
解也有分歧。 一种理解是人民选,人民立(杨幼炯,1984:122;方授楚,
5
2015;梁启超,2016:181-182)。 秦以后,此种“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政
4.“天谴事应”是个别的人事对应于个别的天灾,是君主责任的有限对应。“天谴修德”
则把天谴的对应责任增加到无限,其无限的责任需要由君主的“德”来承担。因此,“天谴
修德”的“德”的无限担当,所显示的是君主政治责任的无限性,体现了政 治关乎天 人关
系这一古老的政治原则(沟口雄三,2014a:22-24)。
5. 梁启超(2016:182)认为,“墨子言:‘明乎天下之乱生于 无正长 ,故选择 贤圣立 为天子
使从事乎一同。 ’孰明之? 自然是人民明。 孰选择之? 自然是人民选择。 孰立之,孰使之?
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 ”但是,萧公权(1998:130-131)反对此种推断,他认为,“就墨子
思想大体推论,则天子之创立殆出于天志,而非由民择。 ”
·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