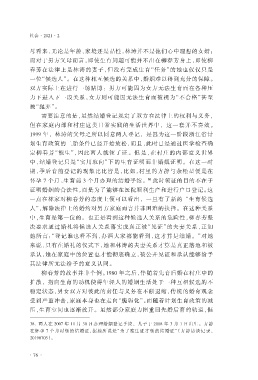Page 83 - 《社会》2021年第2期
P. 83
社会·2021·2
母看来,无论是年龄、家境还是品性,林涛并不是他们心中理想的女婿;
而对于男方父母而言,即使生育问题可能并不出在柳春芳身上,即使柳
春芳在法律上是林涛的妻子,但没有完成生育“任务”的她也仅仅只是
一位“候选人”。 在这种相互候选的关系中,婚姻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双方实际上在进行一场赌博: 男方可能因为女方无法生育而在各种压
力下进入下一段关系,女方则可能因无法生育而被视为“不合格”甚至
被“抛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结婚登记规定了双方在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
但在家庭内部和村庄这类日常实践的生活世界中, 这一套并不奏效。
1999 年, 林涛的父母之所以同意两人登记, 是因为这一阶段浙江省计
划生育政策的二胎条件已经开始放松,而且,此时已经通过医学检查确
定柳春芳“能生”,因此两人就领了证。 但是,在村庄的内部意义世界
中,结婚登记只是“实用取向”下的生育证明而非婚姻证明。 在这一时
期,孕后育前登记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村里的方静与余松星便是在
怀孕 7 个月、生育前 3 个月办理的结婚手续。 38 此时领证的目的不在于
证明婚姻的合法性,而是为了能够在医院顺利生产和进行户口登记。 这
一点在林家对柳春芳的态度上便可以看出, 一旦有了新的“生育候选
人”,解除法律上的婚约对男方家庭而言并非困难的抉择。 在这种关系
中,生育是第一位的。 也正是看到这种候选人关系的危险性,柳春芳坚
决要求通过婚礼将候选人关系落实成真正被“见证”的夫妻关系,正如
她所言:“登记谁也看不到,办酒大家都能看到,这才算是结婚。 ”对她
来说,只有在婚礼的仪式下,她和林涛的夫妻关系才算是真正落地和被
承认,她在家庭中的位置也才能彻底确立,被公开见证和承认能够给予
其法律所无法给予的意义认同。
柳春芳的故事并非个例。1980 年之后,伴随着先育后婚在村庄中的
扩散, 指向生育的动机使得年轻人的婚姻生活处于一种互相候选的不
稳定状态,男女双方对彼此的责任与义务在不断退缩,传统的婚育观念
受到严重冲击,家庭本身也在走向“脆弱化”。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减
压,生育空间也逐渐放开。 虽然部分家庭力图重回先婚后育的轨道,但
38. 两人在 2007 年 11 月 30 日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儿子于 2008 年 3 月 1 日出生。 方静
在怀孕 7 个月时领的结婚证,据她所说是“为了准生证才领的结婚证”(方静访谈记录,
20190703)。
·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