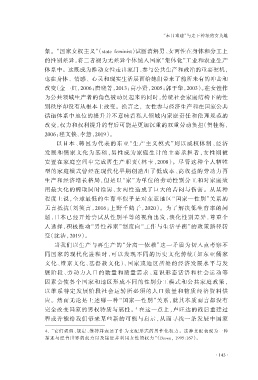Page 150 - 《社会》2021年第2期
P. 150
“末日重建”与走下神坛的女英雄
象。“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t)试图消解男、女两性在身体和分工上
的性别差异,将二者视为无差异个体纳入国家“集体化”工业和农业生产
体系中。 这既成为推动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公共生产和政治的重要契机,
也在身体、 情感、 心灵和现实生活层面给她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
改变(金一虹,2006;唐晓菁,2013;高小贤,2005;郭于华,2003)。在女性作
为公共领域生产者的角色被动员起来的同时,传统社会家庭结构下的性
别秩序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换言之, 女性参与经济生产和在国家公共
话语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并不意味着私人领域内家庭责任和伦理规范的
改变,权力和权利提升的背后可能是更加沉重的双重劳动负担(贺桂梅,
2006;程文侠、李慧,2019)。
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生产主义模式”则以威权体制 、经济
发展和儒家文化为基础,男性成为家庭生计的主要承担者,女性则被
安置在家庭空间中完成再生产职责(林卡,2008)。 尽管这种个人牺牲
型的家庭模式曾经在现代化早期创造出了低成本、高收益的劳动力再
生产和经济增长格局,但是以“家”为单位的劳动性别分工和对家庭效
用最大化的榨取同时给男、女两性造成了巨大的苦闷与伤害。 从某种
程度上说,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似乎是对东亚地区“国家—性别”关系的
无言抵抗(刘笑言,2016;上野千鹤子,2020)。 为了解决低生育率的问
题,日本已经开始尝试从性别平等的视角出发,淡化性别差异,尊重个
人选择,积极推动“男性养家”制度向“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政策路径转
变(沈洁,2019)。
当我们以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依赖”这一矛盾为切入点考察不
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可以发现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东亚儒家
文化、维京文化、基督教文化)、国家或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
展阶段、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需求、意识形态话语和社会运动等
因素会使各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不同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公共家庭政策,
以维系特定发展阶段社会运转所必须的人口 数 量 和物 质 经济 资料 供
应。 然而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国家—性别”关系,就其本质而言都没有
4
完全改变国家的男权特质与属性。 在这一点上,卢旺达的战后重建过
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某些新的可能与启示,从而寻找一条发展中国家
4.“它们强调、规定、维持并表达了作为支配形式的男性化权力。 这种支配表现为一种
描述与经营世界的权力以及接近并利用女性的权力”( Brown, 1995:167)。
·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