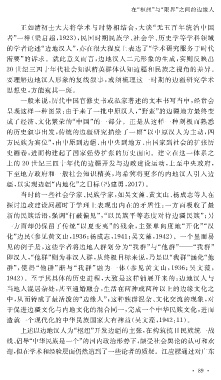Page 96 - 《社会》2020年第1期
P. 96
在 “ 枢纽 ” 与 “ 限界 ” 之间的边缘人
正如清初士大夫将学术与时势相结合 , 大谈 “ 无五百年统治中国
者 ” 一样 ( 梁启超 , 1923 ), 民国时期民族学 、 社会学 、 历史学等学科领域
的学者论述 “ 边地汉人 ”, 亦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 “ 学术研究服务于时代
需要 ” 的诉求 。 就此意义而言 , 边地汉人二元形象的生成 , 实则反映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知识精英群体认知边疆和民族之视角的差异 。
要理解边地汉人形象的复线叙事 , 或须梳理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学术
思想史 , 方能窥其一斑 。
一般来说 , 历代中国官修史书或私家著述的文本书写当中 , 经常会
呈现这样一种图景 : 由于来了一批中原汉人 ,“ 野蛮 ” 的边疆地方最终变
成了经济 、 文化繁荣的 “ 中国 ” 的一部分 。 正是从这样一种刻板而熟悉
的历史叙事出发 , 传统的边疆研究描绘了一幅 “ 以中原汉人为主动 , 四
方民族为宾位 ”, 由中原到边疆 、 由中央到地方 、 由国家到社会的扩张历
史画卷 , 进而构建起了国家强势扩张的历史面向 。 建立在这一体系之
上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开发与边政建设运动 , 上至中央政府 ,
下至地方政府和一般社会知识精英 , 均希冀将更多的内地汉人引入边
疆 , 以实现边疆 “ 内地化 ” 之目标 ( 冯建勇 , 2017 )。
当时的一些社会学家 、 民族学家 , 如吴文藻 、 黄文山 、 杨成志等人在
探讨边政建设问题时于学理上表现出内在的矛盾性 : 一方面吸收了最
新的民族话语 , 强调 “ 打破偏见 ”,“ 以民族平等态度对待边疆民族 ”; 另
一方面却仍保留了传统 “ 以夏变夷 ” 的残余 , 主张单向度地 “ 开化 ”“ 汉
化 ” 边民 ( 参见黄文山 , 1936 ; 杨成志 , 1941 ; 吴文藻 , 1942 )。 一个显而易
见的例子是 , 这些学者将边地人群划分为 “ 我群 ” 与 “ 他群 ”———“ 我群 ”
即汉人 ,“ 他群 ” 则为非汉人群 , 从终极目标来说 , 乃是以 “ 我群 ” 涵化 “ 他
群 ”, 使得 “ 他群 ” 渐与 “ 我群 ” 融为一体 ( 参见黄文山 , 1936 ; 吴文藻 ,
1942 )。 至于其具体的历史进程 , 大致是这样铺展开来的 : 边地汉人与
当地人混居杂处 , 甚至通婚融合 , 生活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边缘文化之
中 , 从而铸成了最活泼的 “ 边缘人 ”; 这种族群混杂 、 文化交流的现象 , 对
于促进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的混合同一 , 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 , 进而
造就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大有裨益 ( 吴文藻 , 1942 : 11 )。
上述以边地汉人为 “ 枢纽 ” 开发边疆的主张 , 在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 倡导 “ 中华民族是一个 ” 的国内政治形势下 , 颇受社会舆论的认可和欢
迎 , 但在学术和经验层面仍然遭到了一些论者的质疑 。 江应 睴 通过对广东
·
8
·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