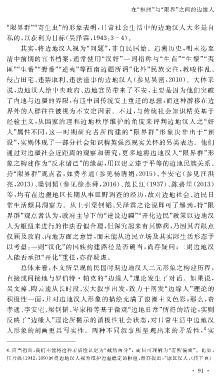Page 98 - 《社会》2020年第1期
P. 98
在 “ 枢纽 ” 与 “ 限界 ” 之间的边缘人
“ 限界群 ”“ 寄生虫 ” 的形象表明 , 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边地汉人大多是自
私的 , 以获利为目标 ( 吴泽霖 , 1943 : 3-4 )。
其实 , 将边地汉人视为 “ 问题 ”, 非自民国始 。 追溯历史 , 明末迄至
清中前期的官书档案 , 通常使用 “ 汉奸 ” 一词指称与 “ 生苗 ”“ 生黎 ”“ 夷
匪 ”“ 生番 ”“ 野番 ”“ 逆夷 ” 等西南边疆所谓 “ 化外 ” 民族交往 , 教唆作乱 、
侵占田宅 、 违禁取利 、 违法滋事的边地汉人 ( 参见吴密 , 2010 )。 大体来
说 , 边地汉人给中央政府 、 边地官员带来了不安 , 主要是因为他们突破
了内地与边疆的界限 , 有违中国传统安土重迁的思想 , 而这种游移在边
界外的人群往往被视为不安定因素 。 不过 , 与传统社会知识精英基于
经验主义 , 从国家治理和边地秩序维护的角度来评判边地汉人之 “ 奸
人 ” 属性不同 , 这一时期研究者所构建的 “ 限界群 ” 形象决非出于 “ 预
设 ”, 实则体现了一部分社会知识精英强烈现实关怀的另类表达 。 他们
通过对边疆社会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 , 更多地将边地汉人 “ 限界群 ” 形
象之构建作为 “ 反求诸己 ” 的缘起 , 用以建立臻于平等的边地民族关系 。
持 “ 限界群 ” 观点者 , 如费孝通 ( 参见杨清媚 , 2015 )、 李安宅 ( 参见汪洪
亮 , 2013 )、 梁钊韬 ( 参见徐杰舜 , 2016 )、 范长江 ( 1937 )、 陈碧笙 ( 2013 )
等 , 均有在边疆地区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经历 , 故对边地社会 、 边民日
常生活颇具洞察力 。 从上引梁钊韬 、 吴泽霖之论说即可了解到 , 持 “ 限
界群 ” 观点者认为 , 政府主导下的 “ 建设边疆 ”“ 开化边民 ” 政策以边地汉
人为枢纽来进行的作法看似合理 , 但深究起来有其弊病 , 乃因其着眼点
仅顾及政府 、 内地方面之意旨 , 而未能从边民立场及其实际生活形态予
以考量 : 一则 “ 汉化 ” 的国族构建路径是否确当 , 尚存疑问 ; 二则边地汉
人能否承担 “ 开化 ” 重任 , 亦存疑虑 。
总体来看 , 本文所呈现的民国时期边地汉人二元形象之构建历程 ,
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 · 帕克的 “ 边缘人 ” 理论发生了对话 。 如果说 ,
吴文藻 、 陶云逵从长时段 、 宏大叙事出发 , 致力于阐发 “ 边缘人 ” 理论的
积极性一面 , 并对边地汉人形象的描绘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 那么 , 费
孝通 、 李安宅 、 梁钊韬 、 岑家梧等基于微观 “ 边地日常 ” 所得的结论 , 实则
反映了 “ 边缘人 ” 理论所揭示的消极性社会状态 , 对日常生活中边地汉
人形象的刻画更具写实性 。 两种不同叙事所呈现出来的矛盾性 , 4 实
4. 应当指出 , 我们不能将这种矛盾性认定为 “ 截然两分 ”, 而只可理解为 “ 有所偏重 ”。 比如 ,
任乃强 ( 1942 : 109 ) 虽将边地汉人视为维护边疆稳定的枢纽 , 然亦提出 :“ 康区汉人 ,( 转下页 )
·
9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