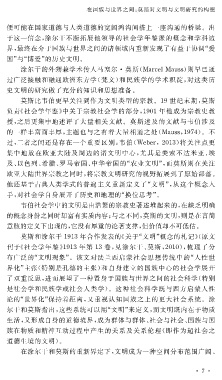Page 14 - 《社会》 2018年第4期
P. 14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便可能在国家道德与人类道德的宽阔鸿沟间搭上一座沟通的桥梁。出
于这一信念,涂尔干不断拓展他领导的社会学年鉴派的概念和学科边
界,最终在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诸领域内重新发现了有益于协调“爱
国”与“博爱”的历史文明。
涂尔干的外甥兼学术传人马塞尔·莫斯( 犕犪狉犮犲犾犕犪狌狊狊 )则早已通
过广泛接触和融通欧洲东方学(梵文)和民族学的学术积淀,对这类历
史文明的研究做了充分的知识和思想准备。
莫斯比韦伯更早关注到作为文明类型的宗教。 19 世纪末期,莫斯
负责《社会学年鉴》中关于宗教社会学的部分, 1901 年他成为宗教史教
授,之后更集中地述评了大量相关文献。莫斯述及的文献与韦伯涉及
的一样丰富而丰厚,主题也与之有着大量相通之处( 犕犪狌狊狊 , 1974 )。不
过,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个重要区别:韦伯( 犠犲犫犲狉 , 2013 )将关注点更
集中地放在欧亚大陆及周边的诸文明中心,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埃
及、以色列、希腊、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的“农业文明”,而莫斯则在关注
欧亚大陆世界宗教之同时,将宗教文明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原始部落。
他还基于古典人类学式的普遍主义重新定义了“文明”,从这个概念入
手,对社会学自身展开了历史和地理的“换位思考”。
韦伯社会学中的文明是由浩繁的宗教史著述堆起来的,在缺乏明确
的概念身份之同时却富有实质内容;与之不同,莫斯的文明,则是在言简
意赅的定义下出现的,它没有厚重的论著支撑,但价值却不可低估。
莫斯和涂尔干 1913 年合作发表的《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原文
刊于《社会学年鉴》 1913 年第 13 卷,见涂尔干、莫斯, 2010 ),梳理了分
布广泛的“文明现象”。该文对法兰西启蒙社会思想传统中的“人性世
界化”主张(特别是孔德的主张)和自身建立的国族中心的社会学展开
了双重反思,进而展望了一种置身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社会科学(特别
是社会学和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这种社会科学既与西方启蒙人性
论的“世界化”保持着距离,又重视认知国族之上的更大社会系统。涂
尔干和莫斯指出,这些系统可以用“文明”来定义,而文明既内在于物质
生活,又形成自身的道德境界,成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国族与国
族在物质和精神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及关系伦理(即作为超社会之
道德生境的文明)。
在涂尔干和莫斯的重新界定下,文明成为一种空间分布范围广阔、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