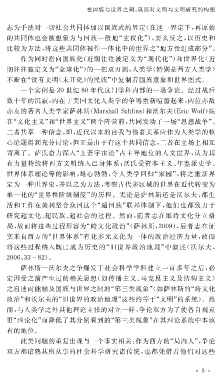Page 12 - 《社会》 2018年第4期
P. 12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志为手法对一切社会共同体加以国族式的界定(在这一界定下,再原始
的共同体也会被想象为与国族一般地“主权化”),要么反之,以历史和
比较为方法,将这些共同体视作一体化中的世界之“地方性组成部分”。
作为同时指向国族化(近期往往被定义为“现代化”)和世界化(近
期往往被定义为“全球化”)的一把双刃剑,人类学(特别是西方人类学)
不断在“没有文明(未开化)的民族”中复制着国族意象和世界图式。
一个实例是 20 世纪 80 年代这门学科内部的一场争论。经过战后
数十年的沉寂,内在于美国文化人类学的争鸣重新喧嚣起来,两位亦敌
亦友的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 犕犪狉狊犺犪犾犾犛犪犺犾犻狀狊 )和沃尔夫( 犈狉犻犮犠狅犾犳 )站
在“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两个阵营前,共同发动了一场“思想战争”。
二者共享一种信念,即,近代以来的自我与他者关系应作为人类学的核
心论题得到充分讨论,但正是由于有这个共同信念,二者在立场上相互
背离了。萨氏奋力深入“土著宇宙论”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世界,认为其
有力量持续将西方文明纳入己身体系;沃氏受资本主义、年鉴派史学、
世界体系理论等的影响,雄心勃勃,令人类学回归“家园”,将之重新界
定为一种世界史,并以之为方法,考察古代多区域的世界在近代转变为
单一化的“世界性阶级制度”的历程。无论是萨林斯还是沃尔夫,都生
活和工作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超国族”联邦体制下,他们也都致力于
研究超文化、超民族、超社会的过程。然而,前者志在维持文化分立格
局,故而将这些过程形容为“跨文化政治”(萨林斯, 2009 ),后者志在证
实来自西方的“世界体系”有化多元文化为一体的政治经济力量,故而
将这些过程纳入既已成为历史的“旧世界政治地理”中叙述(沃尔夫,
2006 : 33-82 )。
萨林斯—沃尔夫之争爆发于社会科学学科建立一百多年之后,必
定因受之前产生过的相关思想(如传播主义、马克思主义及结构主义)
之启迪而能触及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第三类现象”(如萨林斯的“跨文化
政治”和沃尔夫的“旧世界的政治地理”这些约等于“文明”的系统)。然
而,与人类学之外其他理论主张的对立一样,争论双方为了使各自观点
更“理论化”而降低了其分别看到的“第三类现象”在其理论系统中本该
有的地位。
此类问题的重复出现与一个事实相关:作为西方的“局内人”,争论
双方都谙熟其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诸传统,也都凭借着他们对这些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