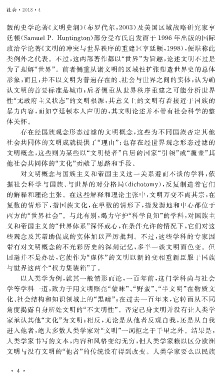Page 11 - 《社会》 2018年第4期
P. 11
社会· 2018 · 4
版的史学论著《文明史纲》(布罗代尔, 2003 )及美国区域战略研究家亨
廷顿( 犛犪犿狌犲犾犘.犎狌狀狋犻狀 犵 狋狅狀 )部分受布氏启发而于 1996 年出版的国际
政治学论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 1998 ),便堪称此
类例外之代表。不过,这两部著作都以“世界”为旨趣,论述文明不过是
为了理解“世界”。前者侧重从诸文明的区域性扩张塑造世界史的总体
形象,而且,并不以文明为普遍存在的、社会与世界之间的实体,认为确
认文明的首要标准是城市;后者侧重从世界秩序重建之可能分析世界
性“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文明根源,其意义上的文明有着接近于国族的
暴力内容,而如亨廷顿本人声明的,其文明论述并不带有社会科学的整
体关怀。
存在经国族观念形态过滤的文明概念,这些为不同国族否定其他
社会共同体的文明成就提供了“理由”;也存在经世界观念形态过滤的
文明概念,这些则为某些以“文明使者”自居的国家“引领”或“覆盖”其
他社会共同体的“文化”贡献了思路和手段。
对文明概念与国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关系避而不谈的学科,依
据社会科学与国族、与世界的对分格局( 犱犻犮犺狅狋狅犿 狔 ),反复制造着它们
的解释和理论主张。在这些解释和理论主张中,文明万变不离其宗,在
复数的情形下,指国族文化,在单数的情形下,指发源地和中心都位于
西方的“世界社会”。与此有别,竭力守护“科学良知”的学科,对国族主
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深怀戒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们对这
些观念及其帮助促成的实体加以严厉批判。不过,这些学科的专家因
带有对文明概念的不光彩历史的深刻记忆,多半一谈文明而色变。但
回避并不是办法,它使作为“虚体”的文明以新的变相重新臣服于国族
与世界这两个“权力集装箱”了。
以人类学为例,就其一般情形而论,一百年前,这门学科尚与社会
学等学科一道,致力于用文明照亮“蒙昧”、“野蛮”、“半文明”在物质文
化、社会结构和知识领域上的“黑暗”;在过去一百年来,它转而从不同
角度揭露自身所处文明的“不文明性”。否定己身文明并没有让人类学
家承认其他“文化”为文明;相反,无论是从他者反观自我,还是从自我
进入他者,绝大多数人类学家对“文明”一词拒之于千里之外。结果是,
人类学家书写的文本,内容和风格变幻无穷,但人类学家赖以区分欧洲
文明与没有文明的“他者”的传统没有得到改变。人类学家要么以民族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