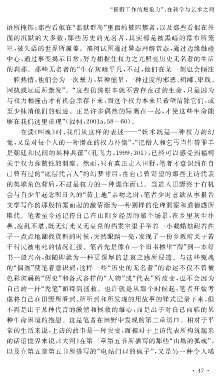Page 54 - 《社会》2018年第1期
P. 54
“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语所掩饰;那些看似在“监狱群岛”里面的被囚禁者,以及那些看似在外
面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历史的无名者,其实都是被黑暗的幕布所笼
罩,被失语的世界所覆盖。福柯试图通过异态理解常态,通过边缘触碰
中心,通过事变揭示日常,努力捕捉住权力之光照亮历史无名者的生活
的刹那。那些无名者的“生存灰暗平凡,不过,他们在某一刻也会倾注
一腔热情,他们会为一次暴力,某种能量,一种过度的邪恶、粗鄙、卑贱、
固执或厄运所激发”。“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
与权力相撞击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它们,或
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正是许多偶然的际遇在一起,才使这些生命能
够在我们这里重现”(福柯, 2001犪 : 58-60 )。
在读《叫魂》时,我们从这样的表述———“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
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
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孔飞力, 1999 : 301 ),已经可以感受到福柯
关于权力弥散性的洞察。然而,只有真正走入田野,笔者才意识到在自
己曾有过的“底层代言人”的幻梦背后,在自己曾寄望的那些上访代表
的英雄角色背后,不过是权力的一种诡诈而已。当进入田野终于有机
会与自少年起念叨日久的“黄土地”亲吻之时,笔者少时意欲从事报告
文学写作的那股拍案而起的激情渐为一种别样的伦理洞察和道德感所
取代。笔者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山阳乡经历的那个场景:在乡里灰尘扑
鼻、凌乱不堪、既无灯光又无桌凳的档案室里手举着一小截蜡烛耐着性
子一点点地翻找资料的时候,突然眼睛一亮,发现了一份乡政府关于若
干村民被电死的情况汇报。笔者先是像在一个旧书摊里“淘”到一本好
书一般兴奋,但随即就为一种更深厚的悲哀之感所浸透。与这些冤魂
的“偶遇”使笔者意识到,这样一些“历史的无名者”的命运不仅不曾被
色彩斑斓的“历史”和各式各样的“人物”或“代表”所改变,也不会因为
自己的一杆“秃笔”而得到拯救。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笔者开始考
虑将自己在田野所看到、所听到和所发现的用故事的样式记录下来,但
不再是出于某种代言的激情和拯救的雄心,而是出于对自己面临的某
种生命困境的抱慰。这是笔者在田野中发现的第二重切口。相对于平
常的生活来说,上访的故事是一种突变,而相对于上访代表所构筑起来
的话语世界来说,《大河》在第三章第五节所描写的那些“山坳的孤魂”,
以及在第五章第五节所描写的“电站门口的疯子”,又是另一种令人唏
· 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