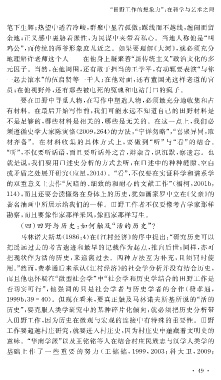Page 56 - 《社会》2018年第1期
P. 56
“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笔下生辉;热望中透着冷峻,群聚中显着孤傲;踩线而不越线,缠闹而留
余地;正义感中裹胁着派性,为民谋中夹带着私心。当地人称他是“叫
鸡公”,而传统的师爷形象庶几近之。如果要理解《大河》,就必须充分
地理解许老师这个人———在他身上凝聚着“新传统主义”政治文化的多
元因子。当然,在他周围,还有敢于担当的王学平,有动辄要表演“与你
一起去滚水”的伍启贤等一干人;在他对面,还有董国光这样老道的官
员;在他视野外,还有那些被电死的冤魂和电站门口的疯子。
要在田野中寻觅人物,在写作中塑造人物,必须最充分地收集和占
有材料。在最后开始写作前,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田野材料是
不是足够的,哪些材料是相关的,哪些是无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
须遵循史学大家陈寅恪( 2009 : 264 )的方法:“宁详勿略”,“喜聚异同,取
材齐备”。 在 材 料 收 集 的 具 体 方 式 上,要 做 到 “听”与 “看”的 结 合。
“听”,不仅要听话语,而且要听话外之音,辩杂音,识沉默,察遗忘。也
就是说,我们要用口述史分析的方式去听,在口述中的种种缝隙、空白
或矛盾之处展开研究(应星, 2014 )。“看”,不仅要在实证科学和谱系学
的双重意义上去作“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福柯, 2001犫 :
114 ),而且还要会读懂烙在身体上的历史,犹如画家罗中立在《父亲》的
著名油画中所展示给我们的一样。田野工作者不仅要像考古学家那样
勘察,而且要像作家那样采风,像画家那样写生。
(四)田野与历史:如何触及“活的历史”?
马林诺夫斯基( 1986 : 4 )在《江村经济》的序中提出:“研究历史可以
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
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
用。”然而,费孝通后来承认《江村经济》的社会学分析并没有结合历史,
而且他也怀疑在“微型社会学”中“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田野工作是
否切实可 行”,他 强 调 的 只 是 社 会 学 者 与 历 史 学 者 的 合 作 (费 孝 通,
1999犫 : 39-40 )。但现在看来,要真正触及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活的
历史”,要克服人类学研究中的某种碎片化倾向,就必须把历史分析带
入田野工作,因为历史在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中有特殊的重要性。田野
工作要超越村庄研究,就要进入村庄史,因为村庄史中蕴藏着文明史的
意味。“华南学派”以及王铭铭等人在结合村庄民族志与汉学人类学的
基础 上 作 了 一 些 重 要 的 努 力 (王 铭 铭, 1999 , 2003 ;科 大 卫, 2009 ;
· 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