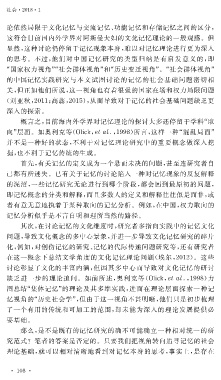Page 115 - 《社会》2018年第1期
P. 115
社会· 2018 · 1
论依然局限于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之间的区分,
这符合目前国内外学界对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的一般观感。但
显然,这种讨论仍停留于记忆现象本身,难以对记忆理论进行更为深入
的思考。不过,他们对中国记忆研究的类型归纳是有启发意义的,即
“国家权力视角”“社会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社会群体视角”
的中国记忆实践研究与本文试图讨论的记忆的社会基础问题密切相
关,但正如他们所说,这一视角也有着很强的国家在场和权力局限问题
(刘亚秋, 2011 ;高蕊, 2015 ),从而导致对于记忆的社会基础问题缺乏更
深入的探索。
概言之,目前海内外学界对记忆理论的探讨大多还停留于学科“取
向”层面。如奥利克等( 犗犾犻犮犽 , 犲狋犪犾. , 1998 )所言,这样一种“混乱局面”
并不是一种好的状态,不利于对记忆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做深入挖
掘,也不利于记忆传统的生成。
首先,有关记忆的定义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甚至连研究者自
己都有所迷失。已有关于记忆的讨论陷入一种对记忆现象的反复解释
的泥沼,一些记忆研究无论进行到哪个阶段,都会回到最原初的问题,
即记忆概念的分类和解释,而且多数人的定义和解释往往似是而非,或
者有意无意地执着于某种取向的记忆分析。例如,在中国,权力取向的
记忆分析似乎是不言自明和理所当然的路径。
其次,在讨论记忆的文化维度时,研究者多指向实践中的记忆文化
问题,导致文化概念的多中心景象,并进一步导致文化记忆研究的碎片
化,例如,对创伤记忆的研究、记忆的代际传递问题研究等,还有研究者
在这一概念下总结文学角度的文化记忆理论问题(埃尔, 2012 )。这些
讨论彰显了文化的丰富内涵,但因其多中心而导致对文化记忆的研讨
缺乏进一步的理论追问。如前所述,奥利克等( 犗犾犻犮犽 , 犲狋犪犾. , 1998 )力
图总结“集体记忆”的理论及其多维实践,进而在理论层面探索一种记
忆视角的“历史社会学”,但由于这一视角不甚明晰,他们只是初步梳理
了一个有用的传统和可加工的范围,却未能为深入的理论发展提供必
要基础。
那么,是不是既有的记忆研究的确不可能确立一种相对统一的研
究范式?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我们把视角转向追寻记忆的社会
理论基础,就可以相对清晰地看到对记忆本身的思考,事实上,是存在
· 1 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