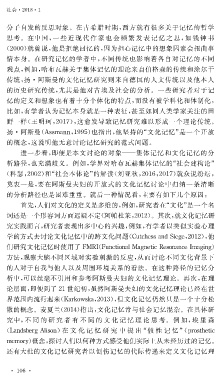Page 113 - 《社会》2018年第1期
P. 113
社会· 2018 · 1
分子自发的反思对象。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很多关于记忆的哲学
思考。在中国,一 些 近 现 代 作 家 也 会 频 繁 发 表 记 忆 之 思,如 钱 钟 书
( 2000 )就曾说,他是拒绝回忆的,因为担心记忆中的想象因素会扭曲事
情本身。在研究记忆的学者中,不同传统也影响着各自对记忆的不同
观点,例如,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来自伯格森的传统和涂尔干
传统,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研究则来自德国的人文传统以及他本人
的历史研究传统,尤其是他对古埃及社会的分析。一些研究者对于记
忆的定义和想象也有着十分个体化的特点,而没有被学科化和体制化,
比如,有学者认为记忆本身就是一种表征,甚至如同人类学家关注的田
野一样(王明珂, 2017 ),这愈发导致记忆研究难以形成一个理论传统。
扬·阿斯曼( 犃狊狊犿犪狀狀 , 1995 )也指出,他坚持的“文化记忆”是一个开放
的概念,这说明他无意讨论记忆研究的范式问题。
进一步看,即便是本文讨论的对象———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分
析路径,也充满歧义。例如,学界对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论”
(科瑟, 2002 )和“社会本体论”的解读(刘亚秋, 2016 , 2017 )就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要在阿斯曼夫妇的开放式的文化记忆讨论中归纳一条清晰
的分析路径也是困难重重。就后一种情况看,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人们对文化的定义是多维的,例如,研究者在“文化”是一个名
词还是一个形容词方面迟疑不定(阿帕杜莱, 2012 )。其次,就文化记忆研
究实践而言,研究者表现出多中心的兴趣,例如,有学者以类似实验心理
学的方式去讨论文化记忆中的跨文化问题( 犆狌狋犮犺犲狊狊犪狀犱犛犻犲 犵 犲 , 2012 ),他
们研究文化记忆时使用了 犉犕犚犐 ( 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犕犪 犵 狀犲狋犻犮犚犲狊狅狀犪狀犮犲犐犿犪 犵 犻狀 犵 )
方法,观察大脑不同区域对实验刺激的反应,从而讨论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人对于自我与他人以及周围环境关系的看法。在这种路径的记忆分
析中,可以丝毫不引用和参考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再次,在理
论层面,即便到了 21 世纪初,虽然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已经在世
界范围内流行起来( 犓犪狉犽狅狑狊犽犪 , 2013 ),但文化记忆仍然只是一个十分松
散的概念。麦夏兰( 2014 )指出,文化记忆常与社会记忆混杂。在具体研
究中,不 同 的 研 究 者 有 不 同 的 文 化 记 忆 理 论 思 考。例 如,埃 里 森
狆
( 犔犪狀犱狊犫犲狉 犵犃犾犻狊狅狀 )在 文 化 记 忆 研 究 中 提 出 “假 性 记 忆”( 狉狅狊狋犺犲狋犻犮
犿犲犿狅狉 狔 )概念,探讨人们以何种方式感受他们实际上从未经历过的记忆。
还有大批的文化记忆研究者以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来定义文化记忆理
· 1 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