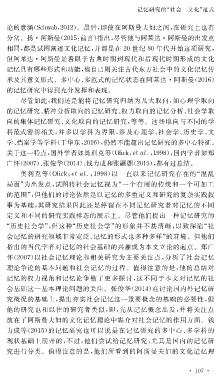Page 114 - 《社会》2018年第1期
P. 114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
论的意涵( 犛犮犺狑犪犫 , 2012 )。最后,即使在阿斯曼夫妇之间,在研究上也有
分岔。扬·阿斯曼( 2015 :前言)指出,尽管他与阿莱达·阿斯曼的出发点
相同,都是试图阐述文化记忆,并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这项研究,
但阿莱达·阿斯曼是着眼于古典时期到现代和后现代时期形成的文化
记忆具有哪些形式和功能,他自己则关注古代东方社会中的文化记忆传
承及其意义形式。多中心、多范式的记忆状态在阿莱达·阿斯曼( 2016 )
的记忆研究中得到充分发挥和表现。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将记忆研究归纳为几大取向,如心理学取向
的记忆研究、精神分析取向的记忆研究、权力取向的记忆分析、社会学取
向的集体记忆研究、文化取向的记忆研究,等等。这些取向与不同的学
科范式密切相关,并多以学科为界限,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
学、档案学等学科(丁华东, 2016 ),仍然不能超出记忆研究的多中心特征。
关于这一特点,国外学者如奥利克等( 犗犾犻犮犽 , 犲狋犪犾. , 1998 ),国内学者如郑
广怀( 2007 )、张俊华( 2014 )、钱力成和张翮隨( 2015 ),都有过总结。
奥利克等( 犗犾犻犮犽 , 犲狋犪犾. , 1998 )以一直以来记忆研究存在的“混乱
局面”为出发点,试图将社会记忆视为“一个有用的传统和一个可加工
的范围”,但他们的讨论依然是以记忆的多重定义和研究的复杂实践叙
事为基础,其研究结果因此还是停留在不同记忆研究者对记忆的不同
定义和不同的研究实践样态的展示上。尽管他们提出一种记忆研究的
“历史社会学”,但这种“历史社会学”的形象并不甚清晰,以致深陷“社
会记忆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记忆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的窘境。但他们
指出的当代学者对记忆的社会基础的兴趣成为本文立论的起点。郑广
怀( 2007 )以社会记忆理论和相关研究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了社会记忆
理论争论的基本问题和社会记忆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总结对
记忆的权力视角和记忆论争做了更多探讨,这不同于本文对记忆的社
会基础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张俊华( 2014 )在讨论国内外记忆研
究概况的基础上,提出夯实社会记忆这一重要概念的基础的必要性,但
他的研究也和以往的研究者类似,即,先从记忆概念出发,并将关注点
放在了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中媒介对社会记忆的作用方面。钱
力成等( 2015 )的记忆研究也可以说是在记忆研究的多中心、多学科的
现状基础上展开的,不过,他们尝试给记忆研究,尤其是国内的记忆研
究进行分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看到的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
· 1 0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