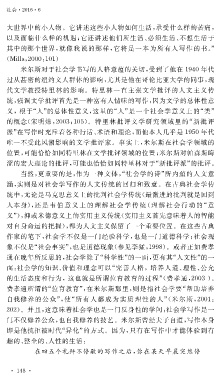Page 155 - 《社会》2016年第6期
P. 155
社会· 2016 · 6
大世界中的小人物。它讲述这些小人物如何生活,承受什么样的苦痛,
以及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它还讲述他们所生活、必须生活、不想生活于
其中的那个世界,就像我说的那样,它将是一本为所有人写作的书。”
( 犕犻犾犾狊 , 2000 : 101 )
米尔斯对于社会学书写的人格意蕴的关切,受到了他在 1940 年代
过从甚密的纽约文人群体的影响,尤其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现
代文学教授特里林的影响。特里林一直主张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传
统,强调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写作,因为文学的总体性意
义,根于“人”的总体性意义,这里的“人”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类”
的概念(宋明炜, 2003 : 105 )。特里林批评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新批评
派”在写作时充斥着各种行话、术语和理论,而他本人几乎是 1950 年代
唯一不受此风潮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事实上,米尔斯在社会学领域的
位置,可能恰恰如同特里林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位置;米尔斯对帕森斯晦
涩的宏大理论的批评,可能也恰恰如同特里林对于“新批评派”的批评。
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体,“社会学的诗”所内蕴的人文意
涵,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和致意。在古典社会学传
统中,无论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社会学传统(最激进的批判就是回到
人本身),还 是 韦 伯 意 义 上 的 理 解 社 会 学 传 统 (理 解 社 会 行 动 的 “意
义”),抑或米德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传统(实用主义首先意味着人的智能
对自身命运的把握),都为人文主义保留了一个重要位置。在这些古典
作家的笔下,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经验科学,也是一门道德科学;社会现
象不仅是“社会事实”,也是道德现象(参见李猛, 1998 )。或者正如费孝
通在晚年所反思的,社会学除了“科学性”的一面,更有其“人文性”的一
面: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可以“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
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费孝通, 2003 )。
费孝通所谓的“位育教育”,在米尔斯那里,则是指社会学要“帮助培养
自我修养的 公众”,使“所 有 人都 成 为实 质理 性的人”(米尔 斯, 2001 :
202 )。并且,这意味着社会学也是一门反身性的学问:社会学写作是一
门不仅修养公众,也自我修养的技艺。米尔斯曾经夫子自道,写作本身
即是他抗拒被时代“异化”的方式。因为,只有在写作中才能体验到有
趣的、整全的、人性的生活:
在四五个礼拜不停歇的写作之后,你在某天早晨突然停
· 1 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