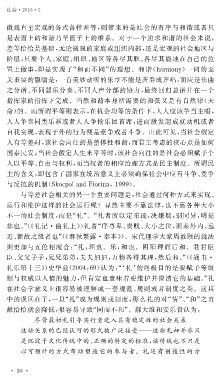Page 37 - 《社会》2016年第5期
P. 37
社会· 2016 · 5
微观直至宏观的各式各样差等,则带来的是社会的有序与和谐或者只
是表面上的和谐乃至面子上的维系。对于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来说,
差等恰恰是基础,无论微观的家庭或组织内部,还是宏观的社会地区与
阶层,只要个人、家庭、组织、地区等各尽其职、各尽其能地在自己的位
置上做事,即是实现了“和而不同”的理想。和谐( 犺犪狉犿狅狀 狔 )一词的至
关重要的隐喻是:一首美妙动听的乐章不能是齐奏或齐唱,而应是乐曲
之分谱、不同器乐分奏、不同人声分部的协力,最终回归总谱并在一个
指挥家的指挥下完成。当然和谐本身所需要的和弦又是有自然律(天
命)的。而所谓平等则表示,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人人应该争当主唱,
人人争奏同类乐器或者人人争抢乐团首席,进而激发起成就动机或者
自我实现,表现于外的行为便是竞争或者斗争。由此可见,当社会假定
人有等差时,该社会向往的是整体性和谐,而君王考虑的核心点是如何
国泰民安;当社会假定人生来平等时,该社会向往的是社会必须赋予个
人以平等、自由与权利,而当权者的相应治理方式是民主制度。所谓民
主的含义,即包含了国家在统治意义上必须确保社会中应有斗争、竞争
与反抗的机制( 犛犽狅犮 狆 狅犾犪狀犱犉犻狅狉犻狀犪 , 1999 )。
与等差社会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
运行和维护这样的社会运行呢?显然主要不靠法律,也不靠各种大小
不一的社会制度,而是“礼”。“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
非也。”(《礼记·曲礼上》)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
近、新故之级者也”(《春秋繁露·奉本》)。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的说法
则更加与五伦相配合:“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通书·
礼乐第十三》)史华兹( 2004 : 69 )认为:“‘礼’的终极目的是要赋予等级
制与权威以人情的魅力,但肯定也意味着要维护并澄清它的基础。”礼
在社会学意义上很容易被理解成一套规范、规则或者制度之类。这其
中的误区在于,一旦“礼”成为规则或制度,那么礼的对“情”、“和”之贡
献恰恰就会降低,很容易导致“同而不和”。郝大维和安乐哲认为:
尽管最初礼引导实行者进入具有稳定性的社会关系———
这些关系的已经认可的形式被广泛接受———这些礼却并非只
是沉淀于文化传统中的、正确的特定的标准,该传统也不只是
以可预计的方式帮助塑造它的参与者。礼还有创造性的方
· 3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