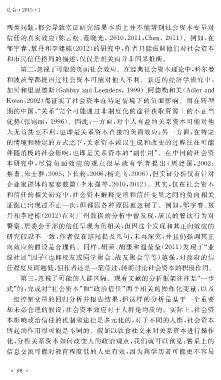Page 105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105
社会· 2015 · 1
两类问题,都会导致实证研究结果本质上并不能辨别社会资本变量对
信任的真实效应(陈云松、范晓光, 2010 , 2011 ; 犆犺犲狀 , 2011 )。例如,在
邹宇春、敖丹和李建栋( 2012 )的研究中,作者只能强调他们对社会资本
和市民信任格局的描述,仅仅是相关而并非因果推断。
第二,忽视了可能的负面社会效应。在经典社会资本理论中,科尔曼
和波茨等都提出过社会资本可能对他人不利。新近的经济学研究中,
加贝和里恩德斯( 犌犪犫犫犪 狔犪狀犱犔犲犲狀犱犲狉狊 , 1999 )、阿德勒和关( 犃犱犾犲狉犪狀犱
犓狑狅狀 , 2002 )都证实了社会资本在特定情境下的负面影响。而在转型
期的中国,“关系”完全可能通过非制度化的途径获取资源上的不正当
优势(张宛丽, 1996 )。因此,一方面,对个人有益的关系资本可能对他
人无益甚至不利,也即是关系资本直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在特定
的情境和特定的方式之下,关系资本赖以生成和改变的过程往往可能
伴随消极的社会影响,也即是关系资本的“副作用”。在中国的社会资
本研究中,尽 管 负 面 效 应 的 观 点 很 早 就 有 学 者 提 出 (周 建 国, 2002 ;
蔡翥、朱士群, 2005 ;卜长莉, 2006 ;杨光飞, 2006 ),但实证分析仅有针对
企业家群体的寥寥数篇(李永强等, 2010 , 2012 )。其实,仅在社会资本
和信任的相关研究中,社会资本解释变量和信任变量之间的负向相关
证据已出现过不止一次,但都因各种原因被忽视了。例如,邹宇春、敖
丹和李建栋( 2012 )在对广州数据的分析中曾发现,居民的餐饮行为对
警察、居委会干部的信任呈现为负相关,但因这个发现和其正向效应的
研究假设不一致,作者仅在结尾提及几句,未再深究,并且仍强调其正
向效应的假设是合理的。同样,胡荣、胡康和温莹莹( 2011 )发现了“业
缘社团”因子(也即校友或同学聚会、战友聚会等等)越强,对政府的信
任程度反而越低,但作者还是一笔带过,转而讨论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第三,忽视了可能的人群区隔。现有文献的分析框架往往是“一步
式”的:完成对“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两个相关的操作化变量,以及
一组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并报告结果,但这样的分析是基于一个重要
却未必合理的假设:社会资本效应对于人群是均质的。实际上,社会资
本影响政治信任的机制和途径是多元化的,对于不同的人群,社会资本
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不同的。假如以饮食社交来对关系资本进行操作
化,分析关系资本如何改变人的政治观点,我们就可以预见:餐桌上的
信息交流可能对教育程度低的人更有效,因为高学历者可能更不容易
· 9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