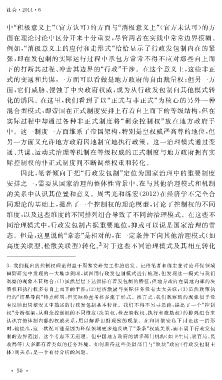Page 57 - 《社会》2014年第6期
P. 57
社会· 2014 · 6
中“积极意义上”(官方认可)的方面与“消极意义上”(官方未认可)的方
面在理论讨论中区分开来十分重要,尽管两者在实践中常常边界模糊。
例如,“消极意义上的应付和走形式”恰恰显示了行政发包制内在的紧
张,即在发包制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承包方常常不得不应对那些自上而
下的打断其过程、冲击其边界的“行政”干涉。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非正
式的变通和共谋,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但另一方
面,它们威胁、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成为从行政发包制向其他模式转
化的诱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正式与非正式”为核心的另外一种
混合型模式,即帝国在正式制度安排上有着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但在
实际过程中却通过各种非正式制度将“剩余控制权”放在地方政府手
中。这一制度一方面维系了帝国架构,特别是皇权威严高尊的地位,但
另一方面又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这一治理模式通过变
通、共谋、运动式治理等机制在等级权威的正式制度与地方政府拥有实
际控制权的非正式制度间不断调整权重和转化。
因此,笔者倾向于把“行政发包制”定位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制度
安排之一,需要从国家治理的整体性背景中、在与其他治理模式和机制
的关系中认识其位置和意义。周雪光和练宏( 2012 )在经济学不完全合
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控制权的理论模型,讨论了控制权的不同
维度,以及这些维度的不同排列组合导致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些不
同治理模式中,行政发包制占据重要地位,抑或可以说是国家治理的常
态。但是,这里说的“常态”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向其他治理模式(如
高度关联型、松散关联型)转化。 3 对于这些不同治理模式及其相互转化
3. 我们提出的控制权理论得益于周黎安研究工作的启发。记得笔者和练宏在讨论环保领域
田野研究中发现的一大堆事例时,试图用行政发包制模式进行梳理,但发现这一模式与我们
观察的现象不甚吻合:( 1 )虽然层层下达指标有着发包制的特征,但地方政府在属地内部的决
策权和执行权多有自上而下的干涉;( 2 )经济激励与实际任务没有太大关联;( 3 )虽然政策执
行的“结果导向”特点鲜明,但实际检查考核多流于形式。换言之,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似乎没
有反映出周黎安文中描述的行政发包制基本特征。我们不得不另寻思路,提出了一个“控制
权”分析框架,从剩余控制权的不同维度(决策权、检查验收权、执行和激励权)的排列组合来
认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威关系,用以解释田野观察的现象。在和周黎安私下讨论这一情形
时,他提出,这一状况可能是因为环保领域更多地反映了“条条”权威关系,而不属于行政发包
制的边界范围。这个考虑不无道理。但中国地方政府的诸多部门机构(如卫生局、教育局、民
政局等)大多都有着类似的任务环境。如何看待这些类似部门与“块块”政府(行政发包制主
体)间关系,是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
· 5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