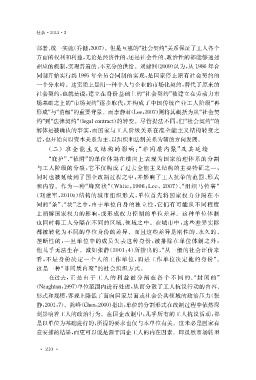Page 217 - 《社会》2013年第3期
P. 217
社会· 2013 · 3
部署、统一实施(乔健, 2007 )。但是互惠的“社会契约”关系保证了工人各个
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无论是经济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都能够通过
相应的机制,实现普遍的、不充分的供给。刘建洲( 2009 )认为,从 1986 年合
同制开始实行到 1995 年全员合同制的实现,是国家停止原有社会契约的
一个分水岭。这实质上是用一种个人与企业的市场化契约,替代了原来的
社会契约,也就是说,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被建立在劳动力市
场基础之上的“市场契约”逐步取代,并构成了中国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再
形成”与“消解”的重要背景。而李静君( 犔犲犲 , 2007 )则将其概括为从“社会契
约”到“法律契约”( 犾犲 犵 犪犾犮狅狀狋狉犪犮狋 )的转变。尽管提法不同,但“社会契约”的
解体是被确认的事实,而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在准全能主义结构转变之
后,也开始向以资本关系为主、以组织和法制关系为辅的方向发展。
(二)准全能主义结构的影响:“非同质内聚”及其延续
“庇护”、“依附”的单位体制在横向上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分割
与工人阶级的分裂,它不仅构成了过去全能主义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
同时也被延续到了国企改制过程之中,并影响了工人抗争的范围、形式
和内容。作为一种“蜂窝状”( 犠犺犻狋犲 , 1996 ; 犔犲犲 , 2007 )、“组织马铃薯”
(刘建军, 2010犪 )结构的城市组织形式,单位首先将国家权力分隔在不
同的“条”、“块”之中,由于单位自身的独立性,它们有可能从不同程度
上消解国家权力的影响,或形成权力控制的单位差异。这种单位体制
也同时将工人分隔在不同的区域、领域之中。在城市中,这些差异实际
都被转化为不同的单位身份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是刚性的、永久的、
垄断性的,一旦单位中的成员失去这种身份,被排除在单位体制之外,
他几乎无法生存。诚如张静( 2001 : 4 )所指出的,“从一般的社会评价来
看,不是身份决定一个人的工作单位,而是工作单位决定他的身份”。
这是一种“非同质内聚”的社会组织方式。
在过去,正 是 由 于 工 人 的 利 益 被 分 割 在 各 个 不 同 的、“封 闭 的”
( 犖犪狌 犵 犺狋狅狀 , 1997 )单位范围内进行处理,从而分散了工人抗议行动的内容、
形式和规模,客观上降低了面向国家层面或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压力(张
静, 2001 : 7 )。陈峰( 犆犺犲狀 , 2000 )指出,单位的分割形式在改制过程中依然深
刻影响着工人的政治行为。在国企改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抗议活动,都
是以单位为基础进行的,所提的要求也仅与本单位有关。这未必是国家有
意安排的结果,而更可以说是源于国企工人的内在因素。即虽然市场转型
· 2 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