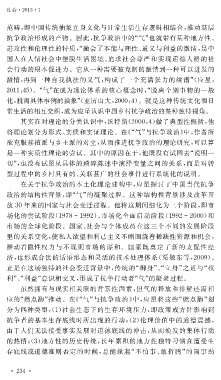Page 241 - 《社会》2013年第1期
P. 241
社会· 2013 · 1
范畴,即中国传统抽象立身文化与日常生活生存逻辑相结合,推动基层
抗争政治形成的产物。因此,抗争政治中的“气”也就带有某种地方性、
进攻性和伦理性的特质,“融会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中
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
会行动的根本促进力。它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
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续谱”(应星,
2011 : 45 )。“气”在成为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时,“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
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亚历山大, 2000 : 4 )。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和日
常生活的相互交织,成为应星认识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某种独特视角。
其实在对理论的分类认识中,沃特斯( 2000 : 4 )做了典型性概括,他
将理论划分为形式、实质和实证理论。在《“气”与抗争政治》中,作者所
欲克服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政治的理论研究,可以算
是一种实质性理论的尝试。其中的原因在于,他既没有试图去“说明一
切”,也没有试图从具体的琐碎陈述中演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是对转
型过程中的乡村具有的、关联甚广的社会事件进行系统化的说明。
在关于抗争政治的本土化理论建构中,应星探讨了中国当代抗争
政治的结构性背景,即“气”的凝聚过程。这种结构性背景涉及改革开
放 30 年来的国家与社会变迁过程。他将这期间细化为三个阶段,即市
场化的尝试阶段( 1978-1992 )、市场化全面启动阶段( 1992-2000 )和
市场的全球化阶段。国家、社会与个体成员在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里的关系变化,使私人欲望和利己主义不断围绕着稀缺性资源和机会,
推动着隐性权力与不规则市场的谋和。国家既奠定了新的支配性经
济,也形成合法的话语形态和灵活的技术处理体系(渠敬东等, 2009 )。
正是在这场独特的社会变迁背景中,传统的“御身”、“立身”之道与“权
利”、“利益”意识相交叉,形成了抗争行动者“气”的凝聚过程。
虽然拥有与现实相关联的背景性因素,但气的释放和排解还需相
应的“燃点酶”推动。在《“气”与抗争政治》中,应星将这些“燃点酶”划
分为四种类型:( 1 )社会生态下的生存环境压力,即政策或方针影响到
抗争者的基本生存底线时所出现的行动;( 2 )伦理价值中的道德震撼,
由于人们无法接受事实发展对道德底线的冲击,从而焕发的集体行动
的热情;( 3 )地方性的历史传统,长年累积的地方性独特习惯在遭受生
存底线或道德准则否定的时候,总能掀起“不怕事、敢折腾”的闹事劲
·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