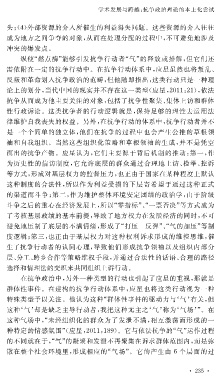Page 242 - 《社会》2013年第1期
P. 242
学术发展与跨越:抗争政治理论的本土化尝试
头;( 4 )外部资源的介入所催生的利益得失问题。这些资源的介入往往
成为地方之间争夺的对象,从而在处理分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
冲突的爆发点。
纵使“燃点酶”能够引发抗争行动者“气”的释放或排解,但它们还
需依附在一定的抗争行动中。在抗争行动体系中,应星虽然也将叛乱、
反叛和革命划入抗争政治的范畴,但他随即指出,这类行动只是一种理
论上的划分,当代中国的现实并不存在这一类型(应星, 2011 : 21 ),依法
抗争从而成为他主要关注的对象,包括了抗争性聚集、集体上访和群体
性行政诉讼。这类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就是,保持足够的理性去运用法
律维护自我丧失的权益。另外,在抗争行动的体系中,抗争行动者并不
是一个个简单的独立体,他们在抗争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公推的草根领
袖和自我组织。当然这些组织化策略和草根领袖的生成,并不是凭空
而出的抗争产物。应星认为,它们主要源于背后机制的推动:第一,作
为历史性的信访制度,它允许底层的群众通过合理地上访、检举、控诉
等方式,形成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压力,也正由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默认
这种制度的合法性,所以作为利益受损的下层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正式
的渠道而斗争;第二,作为维护整体环境安定团结的政治学,由于阶级
斗争之后的重心在经济发展上,所以“零指标”、“一票否决”等方式成为
了考核基层政绩的基本前提,导致了地方权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
避免地压制了底层的不满情绪,形成了“打压—反弹”、“气的加压”等制
度逻辑;第三,也正由于基层权力对这种权利诉求形成的维控思维,催
生了抗争行动者的认同心理,导致他们形成抗争领袖以及组织内部分
层、分工、跨乡合作等策略维权手段,并通过合法性的话语、合理的路径
选择和情理法的交织来共同组织上诉行动。
在抗争政治中,另外一种类型的行动也引起了应星的重视,那就是
群体性事件。在建构的抗争行动体系中,应星也将这类行动视为一种
特殊类型予以关注。他认为这种“群体性事件的驱动力与‘气’有关,但
这种‘气’却是缺乏主导行动者,我把这种无主之‘气’称为‘气场’”。在
这种气场中,“未经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一
种特定的情感氛围”(应星, 2011 : 189 )。它与依法抗争的“气”运作过程
的不同就在于,“气”的凝聚和发泄不再聚集在诉求群体范围内,而是弥
散在整个社会环境里,形成相应的“气场”。它的产生由 6 个层面的过
· 2 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