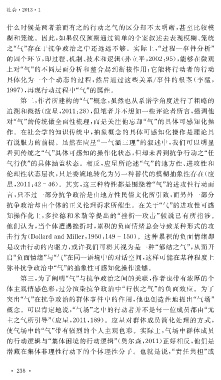Page 245 - 《社会》2013年第1期
P. 245
社会· 2013 · 1
什么时候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行动之气的区分却不太明晰,甚至比较模
糊和笼统。因此,如果仅仅预期通过简单的个案叙述去表现模糊、笼统
之“气”存在于抗争政治之中还远远不够。实际上,“过程—事件分析”
的四个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孙立平, 2002 : 95 ),能够在微观
上对“气”的不同层面分析和整合起到衔接作用;它能将行动者的行动
具体化为一个个动态的过程,然后通过这些关系/事件的根茎(李猛,
1997 ),再现行动过程中“气”的属性。
第二,作者所建构的“气”概念,虽然也从系谱学角度进行了粗略的
追溯和概括(应星, 2011 : 28 ),但笔者并不想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强调他
对“气”的传统做全面性梳理,而是关注他忘却“气”的具体可感知化操
作。在社会学的知识传统中,抽象概念的具体可感知化操作是理论具
有说服力的前提。虽然在应星“一气涵三理”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
看到传统之“气”具体可感知的操作化状态,但却未看到抗争行动之“任
气行侠”的具体涵盖状态。相反,应星所论述“气”的地方性、进攻性和
伦理性状态层次,只是委婉地转化为另一种替代的模糊抽象性存在(应
星, 2011 : 42-46 )。其实,这三种特性都是围绕着“气”的进攻性行动而
言,只不过一部分抗争政治是由地方性民俗文化所引致,而另外一部分
抗争政治却由个体的正义伦理诉求所催生。在关于“气”的进攻性可感
知操作化上,多拉德和米勒等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说已有所指涉。
他们认为,当个体遭遇挫折时,累积的负面情绪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
击行为( 犇狅犾犾犪狉犱犪狀犱犕犻犾犾犲狉 , 1950 : 149-150 )。这种累积的负面情绪即
是攻击行动的内驱力,或许我们可将其视为是一种“郁结之气”,从而开
启“负面情绪”与“气”在同一语境中的对话空间,这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弥补抗争政治中“气”的抽象性可感知化操作遗憾。
第三,为了阐明“气”与抗争政治之间的关联,作者也带有浓厚的个
体主观情感色彩,过分渲染抗争政治中“行侠之气”的负面效应。为了
突出“气”在抗争政治的群体事件中的作用,他也创造性地提出“气场”
概念。可以肯定地说,“气场”之中的行动者并不是每一位成员都由“无
主之气所引导”(应星, 2011 , 189 )。应星对群体成员简化处理的方式,
使气场中的“气”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实际上,气场中群体成员
的行动逻辑与“集体困境的行动逻辑”(奥尔森, 2011 )正好相反,他们是
潜藏在集体非理性行动下的个体理性分子。也就是说,“责任共担”或
· 2 3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