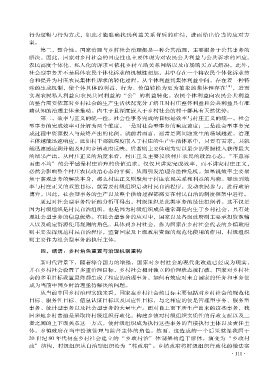Page 113 - 《党政研究》2025年第3期
P. 113
行为逻辑与行为方式,如此才能准确找到利益关系背后的症结,进而给出恰当的应对方
案。
第二,整合性。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都是一种公共治理,主要服务于公共事务的
解决。因此,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回应性也主要体现为对农民公共利益与公共诉求的回应。
农民高度个体化、私人化的诉求可依托乡村互助关系网络以及市场购买方式解决。此外,
社会型事务并不是具体农民个体化诉求的机械性相加,其中存在一个将农民个体化诉求整
合和提升为村庄农民集体性诉求的转化过程。从个体利益到集体利益中间,存在着一种特
殊的生成机制,使个体具体的利益、行为、价值转换为更为抽象的集体性存在 ,进而
〔 18〕
实现农民私人利益向农民共同利益的 “公”的利益转化。农民个体利益向农民公共利益
的整合需要依靠对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状况充分了解且对村庄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具有准
确认知的治理主体来推动。内生于且深度嵌入于乡村社会的村干部具有天然优势。
第三,效率与正义的统一性。社会性事务完成的目标是效率与村庄正义的统一。社会
型事务的完成效率可分解为两个维度。一是对社会型事务的响应速度;二是社会型事务完
成过程中资源投入与最终产出的比例。就前者而言,通常是离问题发生的场域越近,治理
主体越能迅速响应。比如村干部就深度嵌入于村庄的生产生活体系中,只要有需求,其就
能迅速感应到并能及时向乡镇政府反映。后者则主要体现为要以最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
的结果产出。从村庄正义的角度来看,村庄正义主要反映村庄农民的政治心态,“不患寡
而患不均”的公平感是村庄治理的价值追求。仅仅只讲究完成效率,而不讲究村庄正义,
必然会影响整个村庄农民政治心态的平衡,从而引发治理合法性危机。如果说效率主要聚
焦于客观事务的解决本身,那么村庄正义则聚焦于村庄农民关系和利益的均衡。要达到效
率与村庄正义的双重目标,就需要村级组织启动村民自治程序,发动农民参与,进行政治
博弈。因此,社会型事务的生产以及整个供给过程都需要在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中进行。
通过对社会型事务特征的分析可得出,村级组织是此类事务的最佳担纲者。这不仅是
因为村级组织是村民自治组织,也是因为村级组织成员通常都是内生于乡村社会,具有处
理社会型事务的信息优势。在社会型事务的应对中,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则主要承担资源输
入以及确定资源使用规则的角色。具体到乡村社会,作为国家在乡村社会代表的乡镇政府
则主要发挥规范村民自治程序,监督国家及上级政府资源的规范化使用的作用,村级组织
则主要作为社会型事务的执行主体。
四、结语:乡村角色重置与治理机制重构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已经成为现实,
并在乡村社会设置了多重治理目标,乡村社会相对独立的治理状态被打破。国家对乡村社
会的多重目标设置最终都生成了相应的治理事务,如何有效应对来自国家的任务和事务便
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当前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来看,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目标主要包括对乡村社会的规范化
目标、服务性目标、信息认证目标以及回应性目标,与之相应的便是管理型事务、服务型
事务、统计型事务以及社会型事务的大量生产。面对自上而下所生产出来的这些事务,我
国多地乡村普遍是采取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构建乡镇对村级组织实质性的行政支配以及二
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这一方式,使村级组织成为执行这些事务的直接执行主体以及责任主
体。乡镇政府在当中扮演管理与监督主体的角色。然而,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乡村社会建立的 “乡政村治”体制架构趋于解体,演变为 “乡政村
政”结构,村级组织从自治型组织沦为 “村政府”。乡镇政府将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做法实
1 · ·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