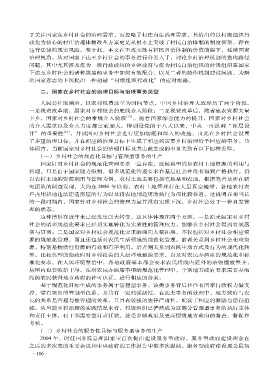Page 108 - 《党政研究》2025年第3期
P. 108
于关注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治理需求,而忽略了村庄内生治理需求,其给出的以村级组织行
政化为核心的村庄治理体制改革方案更是从根本上突破了村民自治体制的制度框架,存在
违背法律的现实风险。鉴于此,本文在不改变既有村民自治体制的价值前提下,延续国家
治理视角,从对国家下达至乡村社会的事务进行分类入手,讨论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路径
问题,其中尤其涉及作为一级行政政权的乡镇政府与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级组织在国家
下达至乡村社会的诸种类型的事务中如何有效配合,以及二者的协作机制建设问题,为解
决国家意志的下沉提出一种超越 “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应对思路。
二、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与治理事务类型
人民公社取消后,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时间节点,中国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税费改革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底线介入阶段;二是税费改革后,随着惠农资源大量
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常规介入阶段 。随着国家综合能力的提升,国家对乡村社会
〔 15〕
的介入需求以及介入力度都空前加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 “顶层设
计”的重要性 ,并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更加彻底和深入的改造,由此在乡村社会设置
〔 16〕
了多重治理目标,并在相应的治理目标下生成了相应的需要乡村治理给予回应的事务。具
体而言,当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及其由此生成的事务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乡村社会的规范化目标与管理型事务的生产
国家针对乡村社会的规范化管理要求一直存在,比较典型的如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与
管理。只是由于国家能力限制,很多规范化管理要求在基层社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仍
以农村土地的资源利用与管理为例,农村土地主要包括宅地基和农地,根据笔者及所在研
究团队的调查发现,大约在 2008 年以前,农村土地管理存在大量真空地带,各地农村农
户占用耕地违法建造房屋的行为以及将农地用途更改的行为都比较普遍。这说明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期内,国家针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力量并没有实质下沉,乡村社会处于一种自发管
理的状态。
这种情形在近年来已经发生巨大转变,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来国家对乡村
社会的诸多规范化要求已经切实地转化为实质性的管理权力,能够在乡村社会得到有效落
实与贯彻;二是国家对乡村社会规范化要求的面向大幅拓展,不仅包括对乡村社会相应资
源的规范化管理,而且还包括对农民生活领域的规范化管理。前者关系到乡村社会相应资
源,特别是物质性资源的有效和有序利用,后者则关系到农民生活方式及行为的现代化转
型。比较典型的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人居环境整治要求,以及对农民办酒席的规范化和标
准化要求。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各地政府基本都会要求农民将院内庭外的杂物摆放整齐,
房屋内也要收拾干净。在对农民办酒席事项的规范化管理中,个别地方政府要求需要办酒
席的农民获得地方政府的许可认证,进行相应的备案。
基于规范化目标生成的事务属于管理型事务,该类事务背后往往有国家行政权力做支
撑,带有突出的管制型色彩,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此类事务的处理中,地方政府与农
民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且具有较强的法律严肃性,配套了相应的激励与惩罚措
施。从当前乡村治理的实践情况来看,村级组织已俨然成为这部分管理型事务的执行主体
和责任主体,村干部需要签订责任状,接受乡镇政府及更高层级地方政府的督查、督促和
考核。
(二)乡村社会的服务性目标与服务型事务的生产
2004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在
之后的多次党的重要会议和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被多次强调。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最初
0 · ·
1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