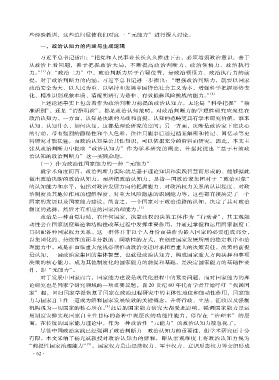Page 64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P. 64
些经验教训,这些追问促使我们对这一 “元能力”进行深入讨论。
一、政治认知力的内涵与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
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 在 “政治三力”中,政治判断力居于首要位置,是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前
〔 1〕
提。对于政治判断力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
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
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
〔 2〕
上述论述事实上包含着作为政治判断力前提的政治认知力。无论是 “科学把握”“精
准识别”,还是 “清醒明辨”,都是政治认知范畴。对政治判断力的学理性研究应聚焦在
政治认知力。一方面,认知是决断的基础和前提,认知的范畴更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谁来
认知、认知什么、如何认知,这都是理论研究的空间;另一方面,决断是政治家下定决心
的行动,带有强烈的隐秘性和个人色彩,往往只能事后通过档案解密和传记、回忆录等史
料研究才能祛魅,而政治认知是公共性知识,可以依据充分的资料而研究。因此,本文主
张从政治判断力中提取 “政治认知力”作为学术研究的概念,并据此提出 “基于有效政
治认知的政治判断力”这一实践命题。
(一)作为政治性国家能力的一种 “元能力”
就学术角度而言,政治判断力实际就是基于理论知识和实践智慧而形成的、能够据此
做出政治决断的政治认知力。而所谓政治认知力,是指一国政治家集团对于 “政治对象”
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包括对政治发展方向的把握能力、对政治权力关系的认识程度、对政
治制度及其地位作用的理解程度、对重大风险隐患的识别能力等,这些都直接决定了一个
国家的发展以及国家能力建设。简言之,一个国家对于政治道路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政治
制度的选择,然后才有相应的国家治理能力。
〔 3〕
政治是一种自觉行动,在任何国家,执掌政权的决策主体作为 “行动者”,其主观能
动性会在国家制度塑造和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通过掌握和运用国家制度工
具调配各种国家权力关系。这一群体并非以个人身份而是作为嵌入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
以集团化的、持续性的而非分散的、间歇性的方式,在创建国家发展所需的稳定秩序和治
理能力中,或是在面临重大危机必须推动政治变迁时承担着重大的决策责任。决策的前提
是认知,一国政治家集团的集体智慧,也就是政治认知力,构成国家重大方向抉择和事项
决策的核心能力,成为其他制度化的国家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是决定国家能力的基础性要
件,即 “元能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能力建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紧要问题,而对国家能力的理
论研究也是国家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有学者开始呼吁 “找回国
家”起,回归国家学派恢复了国家在政治过程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和能动性作用,国家能
力与国家自主性一道成为解释国家发展绩效的关键概念,并将行政、立法、征收以及强制
机构视为一切国家的核心所在。 此后的国家能力研究大都受此影响,强调国家能力是运
〔 4〕
用制度安排实现国家自主性目标的各种中观层次的功能性能力,停留在 “治理术”的层
面。在传统的国家能力理论中,作为一种政治性 “元能力”的政治认知力被忽视了。
尽管中国政治实践已经强调了政治判断力—政治认知力的重要性,但学术研究还十分
有限。本文采纳了杨光斌教授对政治认知力的解释,即从宏观维度上将政治认知力视为
“前提性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权力是由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等交织形成
〔 5〕
2 ·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