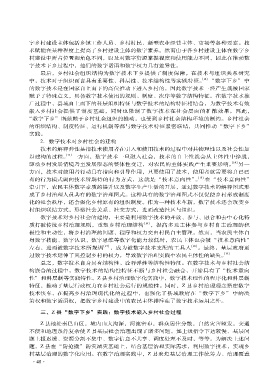Page 50 - 《党政研究》2023年第5期
P. 50
字乡村建设主体包括乡镇工作人员、乡村村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场等各种要素。技
术赋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乡村建设主体的数字素养。然而由于各乡村建设主体在数字乡
村建设中所占位置和角色不同,以及对数字资源掌握程度和使用能力不同,因此在推动数
字技术下乡过程中,他们的数字话语和数字权力具有差异性。
最后,乡村社会组织结构为数字技术下乡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
中,技术对于组织而言具有重要性、科层性、技术结构性等实践特征。 “数字下乡”中
〔 12〕
的数字技术是在国家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下进入乡村的,因此数字技术一经产生就被国家
赋予了特殊意义,具备数字技术使用的规则、制度、次序等数字结构特征。在数字技术推
广过程中,县域自上而下的科层组织特征与数字技术的结构特征相结合,为数字技术有效
嵌入乡村社会提供了制度基础,同时也限制了数字技术在社会层面的扩散效果。因此,
“数字下乡”既依赖于乡村社会组织的推动,也受到乡村社会结构环境的制约。乡村社会
的组织结构、制度特征、运行机制等都与数字技术特征紧密联结,共同推动 “数字下乡”
实践。
2. 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的建构
技术的解释弹性是指技术使用者在引入和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对其物理性以及社会性加
以建构的过程。 一方面,数字技术一旦融入社会,技术的自主性就会从主体性中挣脱,
〔 13〕
驱动乡村发展情境乃至发展形态的整体性变迁,对农民的主体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
〔 14〕
方面,技术对使用者行动具有指向和引导作用,只要使用了技术,使用者就需要将自己已
有的行为模式调向技术所期待的行为方式,这就是 “技术意向性”。 在 “技术意向性”
〔 15〕
牵引下,农民主体数字素质的提升以及数字生产生活的开展,通过数字技术的解释图式形
成了乡村治理人员共有的数字治理图式。这种共有的数字治理图式不仅促使乡村形成制度
化的社会秩序,还会强化乡村原有的组织制度。作为一种技术革新,数字技术还会改变乡
村组织联结方式,形塑社会关系、社交方式,进而改造社区与组织。
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的建构,主要是利用数字技术的开放、参与、融合和去中心化特
质打破传统乡村治理规则,重塑乡村治理结构 ,提高多元主体参与乡村自主治理的积
〔 16〕
极性和主动性,将乡村治理的问题、程序和权力交由村民自主管理。然而,当农民主体自
身数字技能、数字认识、数字思维等数字化能力较低时,农民主体也会被 “技术意向性”
左右,进而被数字技术所规训 ,成为被数字技术支配的工具人 。最终,基层政府通
〔 18〕
〔 17〕
过数字技术延伸了其控制乡村的权力,导致数字治理实践中农民主体性的缺失。
〔 19〕
总之,数字技术自身具有结构性、诠释弹性等结构性特征。在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结
构嵌合的过程中,数字技术的结构性特征不断与乡村社会融合,开始具有了 “技术意向
性”和科层制等实践特性。Z 县乡村治理数字化实践中,数字技术理性的程序化和科层制
特征,推动了基层行政权力在乡村社会运行的规范性。同时,Z 县乡村治理理念搭建数字
技术快车,在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强化了县域政府在 “数字下乡”中的决
策权和数字话语权,把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排斥在了数字技术运用之外。
三、Z 县 “数字下乡”实践: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过程
Z 县地处秦巴山区,境内山大沟深,河流密布,群众居住分散,自然灾害频发。交通
不便和地理条件复杂使 Z 县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上级指令下达较慢、基层问
题上报迟缓、资源分割不集中、数字信息不共享、调度处理不及时,等等。为解决上述问
题,Z 县在 “防抢撤”防灾减灾基础上,结合基层治理实际需求,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乡
村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应用。在数字治理实践中,Z 县聚焦基层治理工作统筹力、治理覆盖
8 ·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