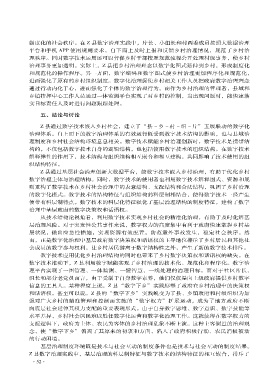Page 54 - 《党政研究》2023年第5期
P. 54
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在 Z 县数字治理实践中,片长、小组长和村两委成员按照大数据治理
平台和手机 APP 使用规则要求,自下而上及时上报和反馈乡村治理情况,规范了乡村治
理秩序。同时数字技术运用还可以督促乡村干部按照规范流程公开处理村级事务,使乡村
治理事务更加透明。实际上,Z 县把乡村治理理念以数字化图式延伸到乡村,形成制度化
和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另一方面,数字编码和数字图式使乡村治理更加程序化和规范化,
进而强化了原有的乡村组织制度。数字化治理促使乡村相关工作人员把政府数字治理理念
通过行动内化于心,进而强化了个体的数字治理行为。而作为乡村治理的管理者,县域和
乡镇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一体监测平台实现了对乡村的控制,当出现问题时,能快速落
实目标责任人及时进行问题跟踪处理。
五、结论与讨论
Z 县通过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建立了 “县 -乡 -村 -组 -片”五级联动的数字化
治理体系。自上而下的数字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既受到数字技术结构的影响,也与县域治
理制度和乡村社会结构环境息息相关。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创新时,数字技术是携带结
构的,不仅包括数字技术自身的逻辑结构,也包括使用数字技术的组织结构。在数字技术
解释弹性的作用下,技术结构与组织结构相互嵌合和相互建构,共同影响了技术使用的组
织结构特征。
Z 县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大数据平台,使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有助于优化乡村
数字治理主体与治理结构。同时,数字技术的使用者也利用数字技术解释图式、资源和规
则重构了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表意结构、支配结构和合法结构,巩固了乡村治理
的数字化模式。数字技术的结构特征与组织结构的科层制相结合,使得数字技术一经产生
便带有科层制特点。数字技术的科层化特征强化了基层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建构了数字
治理中基层政府的数字决策权和话语权。
从技术结构论视角看,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乡村社会的精准化治理,有助于及时化解基
层治理风险。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来说,数字权力的高度集中有利于政府快速掌握乡村基
层状况,做出应急性措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防范意外事故发生,稳定社会秩序。然
而,正是数字化治理中基层政府数字决策权和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排斥了乡村居民和其他社
会成员的数字参与权利,让乡村居民游离于数字结构性之外,产生了新的数字技术排斥。
数字技术应用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数字决策权和话语权的缺失。在
数字技术推动下,Z 县利用数字赋能实现了乡村治理的技术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数字治
理平台实现了一图管理、一体监测、一键智慧、一线处理的治理目标。而对于社区片长、
组长和部分老党员而言,由于受制于自身数字素养,他们仅仅是向上级政府提供乡村数字
信息的工具人。某种程度上说,Z 县 “数字下乡”实践形塑了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决策权
和话语权。甚至可以说,Z 县的 “数字下乡”实践蜕变为了县、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为加
强对广大乡村的精准管理和控制而实施的 “数字权力”扩展运动,成为了地方政府不断
向底层社会延伸其权力支配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自身数字思维、数字意识、数字技能等
水平差异,乡村社会居民难以胜任数字化运营和数字化治理工作。这就使得在数字权力的
支配逻辑下,政府为主体、农民为客体的乡村治理乱象不断上演。这种主客倒置的治理观
念,使 “数字下乡”偏离了其原来的初衷和方向,陷入了政府积极行动、农民消极被动
的行动困境。
基层治理制度环境既是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制度条件也是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制度结果。
Z 县数字治理实践中,基层治理的科层制特征与数字技术的结构特征的相互嵌合,排斥了
2 ·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