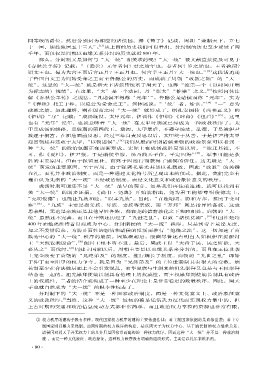Page 82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P. 82
同等级的爵位,然后分别封为相应的诸侯国。据 《荀子》记载,周朝 “兼制天下,立七
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从上面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分封制的历史至少延续了两
〔 11〕
千年,而仅仅是周朝以血缘关系分封的历史就近 800 年。
那么,分封制又是如何与 “大一统”相关联的呢?“大一统”被文献直接提及可见于
《春秋公羊传》记载:“(隐公)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段话追述
〔 12〕
了鲁国自文王为周始受命之王而至鲁隐公的历史,而成就了周朝 “政教之始”的 “大一
统”。这里的 “大一统”就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也即 “推崇一个 (以时间开端
为标志的)统绪”。在这里,“大”是一个动词,乃 “张大”“推崇”之义。 按照何休注
〔 13〕
解 《春秋公羊传》之说法,“凡诸侯不得称 ‘元年’”,鲁隐公是诸侯而称 “元年”,实为
“《春秋》托王于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何休还说:“‘统’者,始也。” “一”意为
〔 14〕
政教之始。如此理解,则在殷商之时 “大一统”就形成了。据孔安国传 《尚书正义》的
《伊训》“序”记载:“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训作 《伊训》《肆命》《徂后》” ,这里
〔 15〕
也有 “元年”纪年,也就意味着 “大一统”在太甲时期就已经成为一种政教秩序了。太
甲是成汤的嫡孙,是殷商的第四代王。最初,太甲暴虐,不遵守汤法,乱德,于是被伊尹
放逐于桐宫,在祖庙面前反思。经过三年自责反思以后,太甲终于从善,于是伊尹将太甲
迎回朝廷并还政于太甲,“以朝诸侯”。 我们从殷商时期诸侯来朝的政治景象可以看到一
〔 16〕
种 “大一统”的政治氛围正在逐渐形成。实际上在成汤战胜夏桀以后, “欲迁其社,不
可,作 《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四海” 。军事可能是获
〔 17〕
胜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保留夏社,而终于因德行而获得了诸侯的信任。这无疑是 “大一
统”萌发的重要原因。至于西周,由于强调礼乐尤其是以礼载政,因此 “政教”的关键
在礼,而礼并非政治制度,而是一种通过文化符号所呈现出来的仪式。据此,我们完全有
理由认为先秦的 “大一统”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文化意义和政治象征意义的秩序。
成汤时期可能还不是 “大一统”最早的萌芽,如果我们再往前追述,就可以找到有
关 “大一统”的诸多证据。 《尚书·尧典》开始就指出,尧为君王能够尊明俊德之士,
“克明俊德”;也能让九族和睦,“以亲九族”。因此,“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
雍” 。“九族”主要是指父族、母族、妻族等亲族,而 “万邦”则是指异姓各族。这意
〔 18〕
思表明,无论是亲族还是其他异姓各族,都在尧的德育教化之下和睦相处。商朝的 “大一
统”虽然还不完善,而且在中期还历经了 “九世之乱”,以致 “诸侯莫朝”, 但国祚延续
〔 19〕
400 年而勉强维持着以商族为中心、分封诸侯的 “大一统”秩序。只是到帝辛荒淫无度,
加之不爱惜民众,为防止百姓的怨情和诸侯的反叛而推行 “炮烙之法”,这一切加速了商
族为中心的 “大一统”秩序的崩溃。周族崛起后,殷商尽管还有明白人如祖伊在提醒纣
王 “天既讫我殷命”, 但纣王根本听不进。最后,周武王以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
〔 20〕
必从之”而伐纣。 周建立国家以后,周朝主要是以血缘关系来分封的,而且在王位世袭
〔 21〕
上完全改变了商朝的 “兄终弟及”的制度,推行嫡长子制度。商朝的 “九世之乱”即始
于仲丁而至阳甲的权力争夺,就是因为 “兄终弟及”的王位世袭制具有很大的变数。嫡
长制至少在合法性层面上不会引发混乱,而华夏族与生俱来的祖先崇拜又总是与王权崇拜
结合在一起的。祖先崇拜使嫡长制具有伦理上的权威性,而王权崇拜则使嫡长制具有政治
上的权威性,二者的结合就构成了一种至少在理论上是非常稳定的政教秩序。因此,周天
子也就自然成为 “大一统”的根本性标志了。
分封制下的 “大一统”不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政治象征意
义的政教秩序。当然,这种 “大一统”最初的确是凭借武力征伐而实现权力集中的,但
①
上古时期的交通和政治信息流动方式都非常简单,而且政治权力掌控的资源也非常有限,
① 权力秩序的建构手段有多种,现代国家权力秩序的建构主要依据法律;君主制国家依据的是血缘世袭;君主专
制国家则以暴力来强制。西周时期的权力秩序的构建,是以周天子为权力中心、基于嫡长制的权力继承关系、
诸侯国对周天子并无权力上的义务只是因伦常而建构的一种权力秩序,因而这种 “大一统”并不是一种政治制
度 ,而是一种文化象征、政治象征。这种权力秩序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以礼乐来维系的。
0 ·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