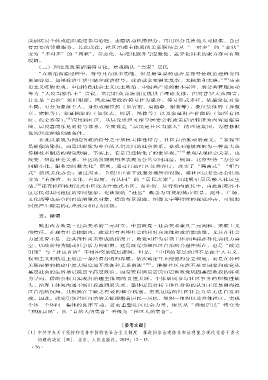Page 78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P. 78
鼓励居民个体或组织通过参与治理、志愿活动积攒积分,再用积分兑换他人可提供、自己
有需要的邻里服务。长此以往,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联结会从 “一对多”的 “伞状”
变为 “多对多”的 “网状”,常态化、标准化服务与应激化、差异化诉求的张力亦可有效
缓解。
(三)理论及政策话语符号化,景观确认 “当家”居民
“在政治沟通过程中,符号具有很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符号使政治理解变得
更加容易。如果政治生活中缺少政治符号,政治就会变得太复杂、太抽象和太难。” 马克
〔 29〕
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新公共管理运动
等为 “人民当家作主”言说、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对普罗大众而言,
什么是 “自治”依旧艰涩,因此需要政治符号作为媒介。符号形式多样,依据象征对象
不同,可分为象征个人、身份或地位的 (如官衔、肩袖章、服装等),象征集体的 (如徽
章、旗帜等),象征抽象的 (如仪式、标语、图像等)以及象征财产价值的 (如所有权
证、代金券等)。 应用到社区,基层党组织可指导居委会将政策话语转译为内容通俗易
〔 30〕
懂、居民喜闻乐见的符号体系,全面营造 “居民是社区当家人”的环境氛围,为潜移默
化的理念灌输创造条件。
在此以景观为例说明政治符号之于居民主体性培育、社区自治推动的意义。“景观不
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
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事实上,它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 景观呈现社会关系,也
〔 31〕
改变、塑造社会关系。社区的景观利用多表现为公共空间再造,例如,北京坚持 “办公空
间最小化、服务空间最大化”原则,通过打造社区公共客厅,改变了 “隔离式” “柜台
式”的机关化办公;通过周末、节假日正常开放服务场所和设施,将社区居委会办公驻地
变为 “有颜值、有文化、有温度、有认同”的 “居民之家”,以此吸引居民融入社区生
活。 还有社区将封闭式小区改为开放式小区,商业街、步行街内嵌其中,由此拓宽各小
〔 32〕
区居民对共同社区的空间想象,化抽象的 “社区”概念为可视的城市街景。此外,广场、
文化墙等也是空间再造的重点对象,借助布景设施、图像文字等持续的视觉冲击,可辅助
居民产生特定的心理效应和行为反馈。
五、结语
跳出西方政党 -社会关系的二元对立,中国政党 -社会关系兼具二元调和、关联主义
的特征。在现有社会体制内,政党具有再塑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和政治能动性,尤其在社会
力量发育不足、公共理性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政党可作为引领主体承担起弥补社会权力真
空、以政治行为撬动社会活力的职责,这是政党引领社区自治的合理性所在,也是 “政党
引领”与 “社区自治”不相冲突的底层逻辑。但是,“中国的基层治理不是在个人主义、
权利主义的轨道上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依次确定互不侵犯的分立领地,而是在各种
关联纽带的构建中最大限度地开发各种关系资源” 。推崇社区自治不是要国家和政党从
〔 33〕
基层社会的生活场景退回至高层政治,而是要以满足居民宜居和政党巩固基层政权的诉求
为导向,借助公权力实现各治理主体间的良性关联。个体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缺
失、治理主体间沟通不畅且权益调剂失灵、整体居民对其主体性身份的认知不足是阻碍社
区自治的沉疴,其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有机团结的社区社会力量无法自发形
成。因此,政党引领社区自治的关键即耦合居民—居民、组织—组织以及整体社区,实现
个体—个体间—集体的良序互动,进而重塑社区社会力量,使其从 “消极居民”转变为
“积极居民”,从 “自然人的集合”升级为 “社区人的集合”。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2 - 13.
6 ·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