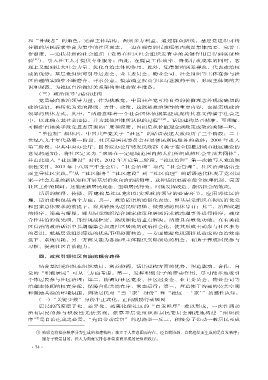Page 76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P. 76
和 “仲裁者”的角色,完善主体结构、调剂多方利益。通过群众路线,基层党组织可将
分散的居民诉求整合为集中的社区意志,一边在现有的行政框架内满足集体需要、完善工
作制度,一边扶持新的社会组织 (党员在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中的关键作用已得到实证检
验 )、引入社工人才提供专业服务;由此,在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同时,客
〔 21〕
观上又起到壮大社会力量、优化自治主体的作用。此外,凭借紧密联系群众、代表政治权
威的优势,基层党组织可引导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参与社
区治理的实践中不断磨合、寻求公意,摸索确立权益争取与让渡的平衡,形成主体间的共
识和规范,为社区自治做好关系架构和社会资本准备。
(三)政治领导与话语建构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可将自身的价值理念外现成确切的
政治话语,再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既是政治领导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政治
领导的具体方式。其中,“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
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话语建构是否精准、可理解、
〔 22〕
可操作直接关乎政党意志贯彻的广度和深度,因而是从价值理念到政策成效的关键一环。
“单位制”解体后,中国共产党关于 “社区”的话语表述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第一阶段,社区是居民委员会开展便民利民服务的载体;2000 年进入
第二阶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 《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
意见的通知》,将社区定义为 “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并由此进入 “社区建设”时代;2012 年开启第三阶段,“社区治理”第一次被写入党的纲
领性文件,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社会治理”取代 “社会管理”,社区治理话语全
面主导社区实践。 从 “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到 “社区治理”的话语迭代体现了党对国
〔 23〕
家—社会关系的新认知和开展基层群众自治的新侧重,这种话语更新在健全治理机制、完善
社区工作的同时,还能更新居民观念、型塑居民行为,间接发挥改造、激活社会的效应。
话语的解释、传播、再建构是社区党组织实现政治领导的必需环节。应用到社区治
理,话语建构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政治话语的通俗化表达,即基层党组织在彻底消化党
和国家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将其转换为居民听得懂、做得到的具体号召;其二,治理议题
的排序、筛选与解释,即基层党组织结合国家政策和居民诉求就治理事务进行排序,确定
合作共治的优先项,再经规范框定、路线细化后重点解决。话语具有教化功能,在有关社
区自治的政治话语中长期濡染会加速社区居民的政治社会化,使其形成主动参与社区事务
的意识。就基层党组织筛选的优先事项协商共治,一方面能避免议题挤兑造成的自治效率
低下、系统内耗,另一方面又能为各治理主体提供实际演练的机会,有助于养成居民参与
习惯、提高社区自治能力。
四、政党引领社区自治的耦合路径
结合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动员、利益协调、话语建构方面的优势,塑造能动、合作、自
觉的 “积极居民”可从三方面考虑。第一,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动作用,尽可能多地吸引
个体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第二,协调好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
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分配,保障合作共治有序、常态运行;第三,营造便于沟通的公共空间
和激励共治的环境氛围,调动居民对 “当 ‘家’身份”和 “社区一 ‘家’”的感性认知。
(一)“关键少数”身份半正式化,正向激励行动居民
居民的高度原子化、差异化、疏离化使社区的 “自发秩序”难以形成,一次性调动
所有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无法实现,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渐进地构建 “组织秩
序”是自治达成之必需。“先富带动后富”的思路举一反三,积极分子带动一般居民可成
①
① 哈耶克将社会秩序分为生成的和建构的:独立于人类意图而存在,经自我协调、自我组织而生成的是自发秩序;
服务于特定目的,经人为刻意安排各种要素而形成的是组织秩序。
4 ·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