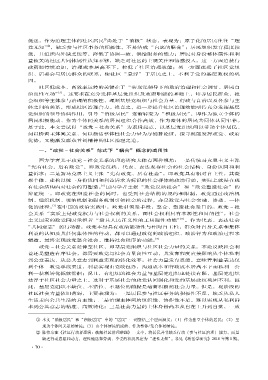Page 72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P. 72
低迷,作为治理主体的社区居民 尚处于 “消极”状态,表现为:原子化的居民往往 “理
①
性无知”,缺乏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不易结成 “自愿的联合”;居民组织发育程度较
②
低,且组织内外缺乏统筹,降低了协调一致、供给服务的能力;居民对身份整体属性和利
益攸关的社区共同体属性认知不够,缺乏对社区的主观关注和情感投入。这一方面迫使行
政资源持续追加,治理成本居高不下,拉低了社区治理效能;另一方面疏远了社区党组
织、居委会与居民群众的联系,使社区 “悬浮”于居民之上,不利于党的基层政权的巩
固。
社区低成本、高效率运转的关键在于 “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
治良性互动” ,这要求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及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培养居民群众、社
〔 5〕
会组织等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理顺基层党组织与社会力量、行政与自治以及各参与主
体之间的关系,形成社区治理合力。换言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亟待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领导协调作用,引导 “消极居民”逐渐转变为 “积极居民”,即作为独立个体的
居民积极能动、作为个体间关系的居民组织合作高效、作为整体的居民共同体认同牢靠。
基于此,本文尝试以 “政党 -社会关系”为逻辑起点,以基层党组织何以带动个体居民、
何以协调主体间关系、何以激活整体性社会力量为序铺排论证,探寻既能发挥政党、政府
优势,又能激发群众首创精神的社区治理之道。
一、“政党 -社会关系”范式下 “耦合”概念的适用性
西方学者关于政党 -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大体有两种视角: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
“先有社会,后有政党”,即政党反映、代表、表达现存社会的社会结构、身份认同和利
益诉求;二是新马克思主义主张 “先有政党,后有社会”,即政党具有相对自主性,其凝
聚个体、建构以统一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为标识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行动,实际上就是在现
有社会结构内对社会的再塑造。 国内学者主张 “政党反映社会”和 “政党塑造社会”的
〔 6〕
辩证统一。即政党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受到社会结构的规约和限制,政党通过政治机
制、组织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机制引领社会的过程,亦是政党与社会交融、渗透、一体
化的过程。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政党引领是手段,整合、塑造社会是目的。政党 - 社
〔 7〕
会关系 “实质上是政党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而社会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目的性”,社会
主义国家的政党同时承担着 “最具人民正义性的工具理性功能” 。作为代表、表达社会
〔 8〕
“共同意志”的行动者,政党本身具有政治能动性与相对自主性,群众对自身关系和集体
利益的认知及其任何集体性的行动,都可以通过政党的政治组织、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来
塑造,最终实现政党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 9〕
政党 -社会关系延伸至社区,即基层党组织与社区社会力量的关系。不论反映社会利
益还是塑造有序社会,都需要政党与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其发育程度直接影响从个体私利
到公意表达、从公共意志到利益实现的转化效率。社会力量发育迟缓,意味着利益表达仅
剩个体—政党单线渠道,利益实现由党政包办,沟通成本和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而私利—公
利—获利转化低效徘徊;况且,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与基层党组织也链接有限,基层党组织
悬浮于社区社会力量之上,这对于基层社会的政党认同强化和党的基层政权巩固不利。因
此,基层党组织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的前提是培育积极的社会力量。但是,现阶段的
社区社会力量依旧薄弱,主要表现为:一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不足,缺乏从私人
生活走向公共生活的自主性;二是治理主体间的组织性、协作性不足,难以实现从私利诉
求到公共意志的精准、高效转化;三是社会力量的主体身份尚未从自在上升到自觉,一致
① 本文 “消极居民”和 “积极居民”中的 “居民”一词囊括三个层面涵义:( 1)作为独立个体的居民;( 2)呈
现为个体间关系的居民;( 3)由个体居民组成的、作为整体/集合体的居民。
② 陈伟东在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一文中,将居民并非缺乏行动 (参与社区治理)能力,而是
缺乏行动意愿和动力,理性地选择旁观、享受的状况界定为 “理性无知”。参见 《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 1期。
0 ·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