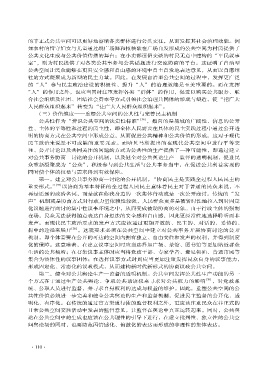Page 112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P. 112
的非正式公共空间可以更好地容纳各类群体进行公共交往,从而发挥其社会治理效能。例
如农村的留守妇女与儿童通过跳广场舞和扭秧歌在广场自发形成的公共空间为村民提供了
公共文化生成与公共价值传播的舞台;在小卖部逗留交谈的村民无意中建构的 “平民议事
室”,则为村民提供了对各类公共事务与公共话题进行交流协商的平台。这证明了自治型
公共空间让民众能够在更具安全感和自由感的环境中自主自发地表达意见,从而以自愿结
社的方式凝聚成为新型的民主力量。因此,在发展自治型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发挥更广泛
的 “人”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提升 “人”的治理效能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发挥
“人”的作用之外,也应当同时注重发挥各类 “群体”的作用,促进以购买公共服务、联
合社会组织及社团、团结社会资本等方式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与塑造,使 “把广大
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转变为 “让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三)价值维度———重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与完善民主机制
公共性作为 “辨识公共空间的决定性标准” ,指向的是场域的广阔性、信息的公开
〔 36〕
性、主体的平等性和过程的民主性,即全体人民需要在具体的民主实践过程中通过公开透
明的协商方式在公共空间中形成公意,从而促进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的形成。这对于现代
民主政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而哈贝马斯提出的在现代公共空间中进行平等交
往、公开讨论以及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方式为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建立
对公共事务协商—讨论的公开机制,以及健全对公共舆论生产—监督的透明机制,促进民
众重新凝聚成为 “公众”,积极参与到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当中,在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
同时使个体的权益与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第一,建立对公共事务协商—讨论的公开机制。“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重要形式。” 以协商为基本特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意味着民主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不
〔 37〕
再是遥远的政治名词,而是就在你我身边的一次集体行动或是一次公开商讨。传统的 “发
声”机制或是协商方式对行政力量依赖性较强,人民群众更多是被暂时性地拉入到对固定
化议题进行商讨的集中性议事环境之中,从而变成被动协商的对象。由于行政主体的强制
在场,民众无法获得随意表达自身想法的安全感和自由感,因此更经常性地选择聆听而非
发声。而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发声方式应该通过更加开放的、民主的、对话的、妥协的、
折中的途径来展开 。这就要求必须在公共空间中建立对公共事务开展协商讨论的公开
〔 38〕
机制,即个体需要在公开的可达的空间内拥有独立、自由交往和发声的权利,并得到制度
化的保障。这意味着,在建立议事空间时应当选择如广场、茶馆、图书馆等更加贴近群众
生活的公共场所;在召集议事主体时应当将党政干部、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普通市民等
集合为整体性的议事团体;在选择议事方式时则应当更加注重发挥民众自身的议事能力,
形成固定化、常态化的议政模式,从而建构新时代新形式的协商议政公共空间。
第二,健全对公共舆论生产—监督的透明机制。公共空间发挥公共性生产功能的另一
个方式在于通过生产公共舆论、争取公共话语权来寻求对公共权力的影响 ,对党政系
〔 39〕
统、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并寻求自身权利的达成与权益的维护。因此,重塑公共空间的公
共性价值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公共舆论的生产和监督机制,促进民主监督的公开化、透
明化、有序化。在传统的通过官方渠道行使的监督权利之外,更应该注重民众在非正式的
日常公共空间交往活动中发表的监督意见,让监督在舆论中真正运转起来。同时,公共舆
论在公共空间中的生成也应该在公共理性的引导下进行,在建立批判性、独立性的公共空
间舆论场的同时,也要防范因情感化、偏激化的表达而形成的非理性的集体表达。
1 · ·
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