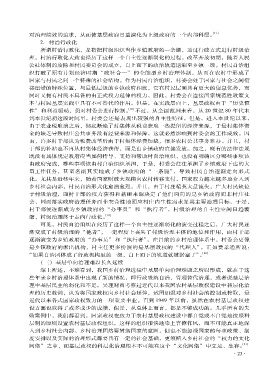Page 24 - 《党政研究》2023年第2期
P. 24
对治理绩效的追求,从而使基层政府日益演化为上级政府的一个内部科层。
〔 17〕
2. 村治行政化
所谓村治行政化,是指把村级组织当作乡镇政府的一条腿,通过行政方式进行村级治
理。村治行政化大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自主性逐渐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人民
公社体制的废除和村民委员会的成立,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退缩至乡镇一级。村民自治组
织打破了原有计划经济时期 “政社合一”的全能型乡村治理体制,从而在农村中形成了
国家与村民之间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衔
接纽带的特殊位置,与最低层级的乡镇政府相比,它在村民层面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而
同时又拥有村民不具备的由正式权力延伸的权力,因此,村委会在连接国家规范性政策文
本与村民基层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基层政权由于 “历史惯
性”和利益驱动,仍对村委会进行控制。 不过,从全国范围来看,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 18〕
到本世纪初这段时间里,村委会还是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特征。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
由于农业税取消之后,彻底断绝了村集体从税费获取一些提留的经济来源,于是村集体资
金的缺乏导致村庄公共事务没有经费来源和保障,这就必然影响到村委会的工作成效。因
而,许多村干部认为税费改革后由于村集体经费短缺,很多农村公共事务难办。并且,村
干部的补贴也不再从村集体经济获得,而是由乡镇政府直接发放。加之,现有的法律法规
既没有具体规定政府应当如何指导、支持和帮助村自治组织,也没有明确区分哪些事项该
由政府完成,哪些事项该由村自治组织承担,于是,村委会往往承担了乡镇政府下达的大
量工作任务,甚至名副其实地成了乡镇政府的 “一条腿”,导致村民自治逐渐走向形式
化。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国家权力越来越多地介入到
乡村社会内部,村民自治形式化愈演愈烈。并且,由于村庄精英大量流失,广大村民缺位
于村级治理,而村干部的权力获得和薪酬来源决定了他们面向的是乡镇政府而非村庄社
会,因而落实政府治理任务而非契合性地回应村庄内生性需求是其主要治理目标,于是,
村干部便逐渐成为乡镇政府的 “办事员”和 “执行者”,村级治理的自主性空间日趋萎
缩,村级治理终于走向行政化。
〔 19〕
可见,村民自治组织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自主性逐渐弱化的演变过程之后,广大村民逐
渐变成了村级治理的 “他者”,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村级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而村干部
逐渐演变为乡镇政府的 “办事员”和 “执行者”。在目前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村委会更像
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村主任更多扮演的是基层政权的 “代理人”。正如费孝通所说:
“如果自治团体成了行政机构里的一级,自上而下的轨道就被淤塞了”。
〔 20〕
(三)基层单向治理难以长久延续
综上所述,不难看到,我国乡村治理进程中基层单向治理难题之所以形成,就在于这
些年来乡村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新的情况,即行政吸纳自治,管理替代治理,或者说基层治
理中基层民主的弱化和不足。吴理财曾考察过近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科层化治
理的历史教训,认为将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延伸,试图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或榨取,是
近代以来各式国家政权致力的一项重要事业。直到 1949 年以前,虽然在农村基层政权建
设方面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绩,但是,从总体上而言,都是不够成功的。几乎所有的失
败案例中,我们都看到,国家政权在致力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科
层制的原则设置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样的组织很快地染上官僚作风,而不可能真正地深
入到乡村社会内部。乡村治理固然要贯彻国家的意图,但也不能忽视国家的每项政策、制
度安排以及实际的治理形式都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更须植入乡村社会的 “权力的文化
网络”之中,而基层政权的科层化治理根本不可能在这个 “文化网络”中立足、生存。
〔 21〕
3 ·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