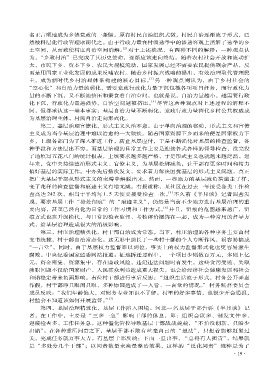Page 20 - 《党政研究》2023年第2期
P. 20
名正言顺地成为乡镇党政的一条腿。原有村民自治组织式微,村民自治逐渐流于形式,已
然被科层化行政管理取而代之。由于行政力量在村级选举中的渗透客观上消解了选举的乡
土空间,从而致使村庄自治空间消解。 对于上述状况,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
〔 2〕
为,“乡政村治”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逐渐应该走向终结。随着农村社会开放和流动扩
大,市民下乡、资本下乡、农民大规模流动,国家发展已经不需要农民提供剩余产品,反
而是用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成果反哺农村。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效治理取代管理民
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核心目标。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乡村社会的
〔 3〕
“空心化”和自治力量的弱化,需要党政行政化力量下沉包揽各项项目任务,而行政化力
量的不断下沉,又不断地挤压和蚕食着自治空间。也就是说,自治力量越小,越需要行政
化下沉,行政化力量越强势,自治空间越被挤压。 尽管这两种观点对上述过程的解释不
〔 4〕
同,但都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基层自治力量不断弱化,党政行政力量替代乡村公共权威成
为基层治理主体,村民自治走向形式化。
第二,基层治理官僚化,形式主义久治不愈。由于单向治理的驱动,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成为当今基层治理中难以治愈的一大顽疾。随着国家资源下乡而来的便是国家权力下
乡,上级各部门为了深入推进工作,防止基层应付,于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的检查监督,各
种手段和方法层出不穷。而基层治理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迎接各式各样的督导检查,没完没
了地填写五花八门的统计报表,上级要求越多越严格,于是形式主义也就越来越泛滥。近
年来,党中央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
搞好基层的实际工作。中办先后数次发文,要求着力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真正
把广大基层干部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然而,一些地方的基层减负措施走了样,
变了花样的检查监督和痕迹主义有增无减。有报道称,某社区在过去一年接受各类工作检
查高达 242 次,相当于平均每 1. 5 天便要接受检查一次。 不久前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
〔 5〕
现,要求基层工作 “处处留痕”的 “痕迹主义”,仍然是当前不少地方进行基层治理的重
要内容,甚至已经内化为日常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 并且,留痕的范围越来越广,留
〔 6〕
痕方式也在升级换代,与日常的检查监督、考核评价捆绑在一起,成为一种常用的督导方
式,给基层治理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
第三,村庄治理精英化,村干部自治成为常态。当下,村庄治理的各种事务主要由村
支书统揽,村干部自治常态化。这无形中助长了一些村干部的个人专断作风,很容易搞成
“一言堂”。同时,由于基层权力监督难以到位,事实上的权力监督形式化也更容易滋生
腐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报道:征地拆迁过程中,一个项目少则数百万元,多则上亿
元,资金密集、资源集中,存在廉政风险,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这些贪污受贿、失职
渎职问题不仅给国家财产、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也会给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
和谐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有位村干部进行事后反思:“组织生活流于形式,村务公开弄虚
作假,村干部睁只眼闭只眼,多种原因造成了一人管、一言堂的情况。”村务监督委员会
成员反映:“我们年龄偏大,对财务专业知识不了解。村里的好多事情,也很少开会通报,
村监会不知道该如何开展监督。”
〔 7〕
第四,基层治理精致化,基层工作陷入困境。河北一名基层干部告诉 《半月谈》记
者,在工作中,主要是 “三多一急”影响干部的休息,即:组织会议多、制发文件多、
迎接检查多、工作任务急。这种僵化管控导致基层干部战战兢兢,“不怕没创新,只盼少
出错”。在各种重压问责之下,基层干部不敢有丝毫自己的 “想法”,只想着能够赶紧过
关,完成任务就万事大吉。有基层干部反映:下面一旦出事,“总得有人担责”,结果就
是 “多处分几个干部”;以问责数量来衡量整治效果,这样的 “泛化问责”纯粹是为了
9 ·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