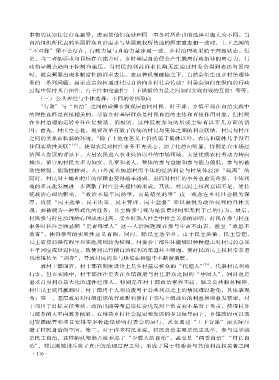Page 118 - 《党政研究》2022年第4期
P. 118
事物的认知往往存在差异,进而使他们在处理同一事务时所作出的选择可能大为不同。当
自治组织所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需求与基层政权所传递的国家意志相一致时,上下之间的
“不对称”便不会存在,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步履一致,乡村治理效果趋于理想状态。但
是,当二者的诉求与目标存在偏差时,乡村基层自治便会产生脱离行政指导的离心力,行
政指导则会趋向于控制和施压。当村民的利益诉求长期无法通过村委会得到表达与回应
时,就会频繁出现非制度性的诉求表达。在这种机制碰撞之下,自然会衍生出乡村治理体
系的一系列问题:国家意志如何通过村民自治向乡村社会传递?村委会如何在纵向的行政
过程中保持其自治性、自主性和完整性?上下纵横的力量之间如何实现有效的互嵌?等等。
(三)公共理性与个体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
“行政”与 “自治”之间的碰撞在微观层面同村民、村干部、乡镇干部在自治实践中
的理性选择是直接相关的。尽管乡村基层群众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和直接作用对象,但村民
在乡村治理的运转中往往是被动、消极的,这种低度参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诱
因:首先,村庄空心化。税费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村民与集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村民与村庄
之间的关系面临新的环境,“除了土地在名义上仍然属于集体以外,农民和集体几乎没有
任何实质性关联” ,使得农民对村庄事务不再关心,原子化趋向明显。特别是在市场经
〔 22〕
济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入农业经济以外的市场领域,大量优质农村劳动力转向
城市,留守的村民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整体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偏低,参与的被
动性较强、能动性较弱。人口外流在加剧村民个体的经济利益与村集体经济 “疏离”的
同时,村民对土地和村庄的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弱,进而对村庄的事务也愈发冷漠,个体利
益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离散了村庄公共理性的形成。其次,村民民主权利意识不足。受传
统政治心理的影响, “政治不是平民的事,而是精英的事”这一观念在乡村社会极为深
厚,致使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难以被视为政治权利的具体实
现,而被视为一种形式化的任务,甚至将参与视为是浪费时间和无利于己的行为。最后,
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心理成本过高。受乡村熟人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影响,村民在参与村庄
事务时往往会顾忌到 “是否得罪人”这一人情问题而在参与中言不由衷,甚至 “敢怒不
敢言”,使得参与的实质性意义有限。同时,除民主选举外,由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的操作程序和实施规则较为模糊,村委会干部往往能够以种种理由对村民的意见
不予回应或延迟回应,致使村民行使自治权利的渠道并不畅通,使村民的民主权利常常遭
到漠视甚至 “剥夺”,导致村民的参与热情在碰壁中不断被消磨。
就村干部而言,村干部在制度设计上是乡村基层群众的 “代理人” ,代表村民利益
〔 23〕
行事。但在实践中,村干部往往是夹在乡镇政府与村庄群众之间的 “中间人”,同时也是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特别是在村干部政治素养不高、缺乏公共服务精神、
村庄民主监督羸弱时,村干部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情况难以避免,具体表现
为:第一,基层政府对村级组织的行政影响使村干部与上级政府的利益捆绑愈发紧密,村
干部出于目标责任考核、政治出路等考量往往会优先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使得村务
与政务的天平向政务倾斜。在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多目标导向下,乡镇政府可以通
过资源配置和项目安排等多种途径影响村委会的运行,甚至通过 “上下合谋”而实际压
缩了村民自治的空间。第二,对于许多村民来说,村民自治主要是民主选举,参与选举就
是民主自治,这样的认知偏差滋养起了 “少数人的自治”,甚至是 “两委自治”“村长自
治”,村民则被排斥在了真正的治理过程之外,形成了属于村委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
1 · ·
1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