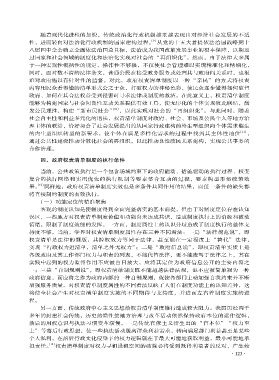Page 125 - 《党政研究》2022年第2期
P. 125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政治化行政机制越来越表现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
性,进而转向对法治化行政机制的国家建构过程。 从党的十五大首提依法治国战略到十
〔 9〕
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法治成为我国改革发展事业的根本保障,以期通
过国家和社会领域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实现对社会的 “再组织化”。然而,由于法律大多属
于一种宏观性概括性的规定,操作性不够强,不仅使社会管理难以实现精准化和精细化,
同时,面对数不清的法律条文,普通公民在接受政务服务或处理其与政府间关系时,也很
难对政府施以有针对性的监督。对此,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以一种 “亲民”的方式将权责
内容用民众看得懂的清单形式公之于众,打破权力的神秘色彩,使民众逐步懂得如何监督
政府、如何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寻求法律或制度的救济。在此意义上,权责清单制度
能够为构建国家与社会间良性互动关系提供有效工具,使无序化的个体实现彼此联结,激
发公民理性,构建 “新市民社会” ,以此实现对社会的 “再组织化”。与此同时,随着
〔 10〕
社会自主性和利益多元化的增长,权责清单制度对政府、社会、市场及公民个人等地方治
理主体的联结,恰好契合了社会发展提出的从国家行政建构的外生型组织向个体需求催生
的内生型组织转型的新要求,使个体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过程中找到其主体性地位 ,
〔 11〕
通过公共性建设推动分散化社会的再组织,以此推动良性政民关系建构,实现公共事务的
合作治理。
四、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执行条件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是一个包含场域约束下的政府能动、措施驱动的执行过程、权变
复合的执行网络和实用优先的执行机制等要素整合互动的过程,要素构型形塑政策效
果。 同样地,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效也是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任一条件的缺失都
〔 12〕
将直接制约制度的有效执行。
(一)功能定位的精准聚焦
客观的制度认知是使制度得到全面完整落实的基本前提,但由于对制度定位存在认知
误区,一些地方对权责清单制度价值和功能尚未达成共识,造成制度执行上的消极和被动
情绪,限制了制度效能的发挥。一方面,制度属性上的认识分歧造成了制度执行的整体支
持度不够。当前,学界对权责清单制度属性存在三种不同看法:一是 “法律规范说”,即
权责清单是法律的翻版,其控权效力等同于法律,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 “替代”法律,
实现 “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二是 “政府信息说”,即权责清单实质上是
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与职责的列表,不能代替法律,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其在
实践中起到的权力监督作用不应被盲目放大,应将其定位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之
一;三是 “自制规则说”,即权责清单制度既不能超越法律法规,也不应被简单视为一种
政府信息,而应将之作为政府内部的一种自制规则,促使各部门主动加强自我约束并不断
增强服务质量。对权责清单制度属性的不同看法反映了人们在制度功能上的认知差异,这
将使全社会产生对权责清单制度实施的不同期待与支持度,并进而左右着制度实施的进
程。
另一方面,传统政府中心主义思想给权责清单制度推行造成较大阻力。我国历经两千
多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历史的惯性使地方治理与改革活动依然保持政府本位的运作逻辑,
落后的用权意识与执法习惯变革缓慢。一是传统官僚主义衍生出的 “官本位” “权力至
上”等落后行政思想,使一些执法活动脱离群众利益需求,转向满足部门利益甚至是某些
个人私利。在落后行政文化侵染下的权力逻辑就在于最大可能地获取利益,最小可能地承
担责任。 权责清单制度对权力寻租设租空间的破除必将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产生较
〔 13〕
2 · ·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