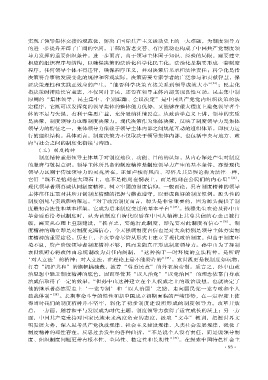Page 94 - 《党政研究》2021年第5期
P. 94
实现了领导集体交接的规范化,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难题,为制度领导力
的进一步提升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干部的新老交替、有序流动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制度领
导力发挥的重要组织条件。进一步而言,由于领导主体囿于知识、经验的局限,需要建立
相应的组织程序与结构,以确保决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是指要形成一套制度
程序,任何领导个体不得违背,确保程序正义,并对决策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科学化是指
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客观实际,决策需要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和贡献智慧,保
证决策理性和实践正效应的产生,“能否科学决策直接关系到领导成效大小” ;民主化
〔 23〕
指决策时排除长官意志,不仅问计于民,还要在领导主体内部实现良性互动。民主集中制
原则的 “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组织决策的法
定程序,它既可以发挥党的领导集体的整体能力优势,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领导者个
体的不足与失误,有利于集思广益,充分吸纳社情民意。从政治学意义上讲,领导的实质
是决策,制度领导力也即制度决策力。现代决策作为集体决策,反映了制度领导力是集体
领导力的特征之一,集体领导力依赖于领导主体内部之间规范互动的组织体系,即权力运
行的组织结构。具体而言,制度决策力不仅取决于领导集体内部,也包括中央与地方、政
府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衔接与沟通。
(三)制度精神
制度精神意指领导主体基于对制度地位、功能、目的的认知,从内心深处产生对制度
的服膺与敬畏意识。领导主体所具备的制度精神是制度领导力产生的基本条件,亦是现代
领导力区别于传统领导力的灵魂所在。正如卢梭将风尚、习俗尤其是舆论称为法律一样,
它们 “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
〔 24〕
现代领导者须真诚认同制度精神,树立牢固的制度信仰。一般而论,具有制度精神的领导
主体往往注重对其所开创制度精髓的把握与模范遵守,以形成良好的制度惯例。源头性的
制度创见与实践影响深远,“对于政治制度而言,源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源头提供了制
度最初合法性和基本框架,它成为后来制度变迁的基本平台” 。钱穆先生在论及孙中山
〔 25〕
革命后重拾考试制度时,认为该制度自清代以后在中国人精神上共尊共信的心念已被打
破,需要从心理上重新建设,“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 。制
〔 26〕
度精神的确立即是对制度充满信心,今天强调制度自信也是对大众特别是领导主体夯实制
度精神的重要途径。历史上,辛亥革命尽管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但由于制度环
境不良,资产阶级领导者制度精神不够,因而未能真正形成制度领导力。孙中山为了抑制
袁世凯野心将政体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 “这种拘于一时环境的立法精神,是所谓
‘对人立法’的精神;对人立法,在理论上是不能赞许的” 。袁世凯更是视制度如玩物,
〔 27〕
打着 “拥护共和”的旗帜搞独裁,披着 “尊重民意”的外衣搞帝制。质言之,孙中山政
治思想中缺乏制度精神的底色,因而尽管其 “以人治党”“以党治国”的理念依靠自身政
治威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孙中山这种建立在个人权威之上的政治设想,也就决定了
他的继承者必然要走上 ‘一党专制’和 ‘以人治国’之路,走向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
独裁体制” 。长期革命斗争的惯性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严峻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使
〔 28〕
得当时我们的制度精神并不坚牢,弱化了初步制度建设所形成的制度领导力。改革开放
后,一方面,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制度领导力获得了适宜成长的沃土;另一方
面,中国共产党秉持对国家民族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汲取 “文革”教训,把握世界文
明发展大势,深入思考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强化了
制度精神的理性存在。反思过去发生的各种曲折,“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
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 29〕
3 · ·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