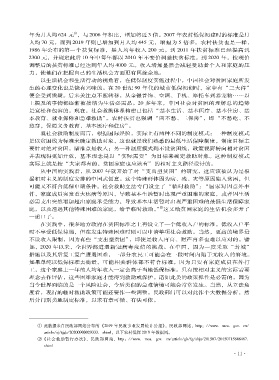Page 12 - 《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P. 12
年为月人均 624 元 ,与 2006 年相比,增加将近 3 倍。2007 年农村低保初建时的标准是月
①
人均 70 元,而到 2019 年则已增加到月人均 445 元,增幅为 5 倍多。农村扶贫也是一样,
1986 年公布的第一个扶贫标准,是人均年收入 200 元。到 2011 年扶贫标准已经提高到
2300 元,并规定此后 10 年中每年都以 2010 年不变价调整扶贫标准。到 2020 年,按现价
调整后的扶贫标准已经达到年人均 4000 元。收入增加显然会减轻受助者个人和家庭的压
力,使他们在把握自己的生活机会方面更有回旋余地。
以生活机会和生活行动的视角看,在低保制度实施过程中,中国社会对贫困家庭所发
生的心理变化也是饶有兴味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城市低保初创时,家中有 “三大件”
便会受到质疑。后来关注点不断转移,从金银首饰、空调、手机、摩托车到养宠物……以
上提及的事物都逐渐被接纳为生活必需品。20 多年来,中国社会对贫困的理解总的趋势
是宽松和包容的。现在,社会救助体系构建已包括 “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基本住房、基
本教育、就业保障和急难救助”。农村扶贫也强调 “两不愁、三保障”,即 “不愁吃、不
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就社会救助制度而言,根据国际经验,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一种制度模式
是以贫困线为标准来确定救助对象,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制度目标主
要针对绝对贫困,瞄准点是收入;另一种制度模式则不设贫困线,政策视野转向相对贫困
并表现得更加开放,基本理念是以 “实际需要”为目标来确定救助对象。这种制度模式
实际上就是按 “大家都有的,贫困家庭也应该有”的相对主义路径设计的。
从中国的实践看,从 2007 年就开始了对 “支出型贫困”的研究,这应该被认为是根
据相对主义的制度安排的中国式创意。这个特殊群体因为病、残、灾等原因陷入贫困,但
可能又不符合低保申请条件。社会救助立法专门设立了 “临时救助”:“国家对因意外事
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因生活
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这又给贫困家庭的生活机会多开了
②
一道口子。
在实践中,很多地方政府在贫困标准之上再设立了一个低收入户的标准。低收入户平
时不享受低保待遇,但在发生特殊困难时则可以申请单项社会救助。当然,更高的境界是
不设收入限制,因为有些 “支出型贫困”,即使是收入再高、财产再多也难以应对的。譬
如,2020 年以来,全世界都遭遇新冠病毒疫情的挑战。在中国,因为一度采取 “封城”
措施以及其后复工复产遭遇困难,一部分农民工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陷于无收入的窘境。
如果单纯以低保标准去衡量,可能相关群体都不符合标准。因为只要有家庭成员在外打
工,这个家庭上一年的人均年收入一定会高于当地低保标准。只有按相对主义的实际需要
理念去作评估,这些困难家庭才能得到救助或保护。诸如此类的政策弹性是必需的,因为
当今世界面临的是一个风险社会,今后类似的急难情境可能会常常发生。当然,从立法角
度看,现行的临时救助政策可能还要作一些调整。民政部门可以对此作个大数据分析,然
后分门别类地制定标准,以求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① 此数据来自民政部网站公布的 《 2019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网站,http:/ / www. mca. gov. cn/
article/ sj/ tjgb/ 20200900029333. shtml,以下农村低保 2019年数据同。
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民政部网站,http:/ / www. mca. gov. cn/ article/ gk/ fg/ shjz/ 201507 / 20150715848487.
shtml
1 ·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