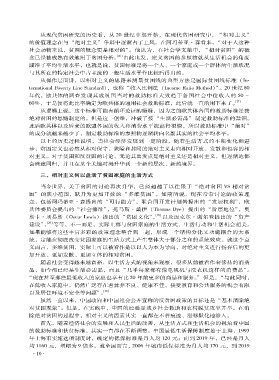Page 11 - 《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P. 11
从现代贫困研究的历史看,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在现代贫困研究中, “相对主义”
的价值理念在与 “绝对主义”争辩中逐渐占了上风。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对于人这种
社会动物来说,贫困的概念更是相对的”。他认为,在社会学文献中,“相对贫困”的概
念已经被成熟有效地用于贫困分析。 由此出发,定义贫困的参照物就从生活机会的角度
〔 26〕
瞄准了平均生活水平,也就是说,贫困标准是将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群体的生活状况
与其所在的特定社会中占主流的一般生活水平作比较后得出的。
从操作层面讲,以相对主义的思路来测量贫困线的典型方法是国际贫困线标准 ( In
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也称 “收入比例法 ( Income Ratio Method)”。20 世纪 80
年代,欧共体的调查发现其成员国当时的救助标准大致趋于各国社会中位收入的 50 ~
60%,于是便将此比率确定为欧共体的通用社会救助标准,此后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 27〕
从逻辑上说,这个标准可能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因为之前欧共体各国的救助标准是按
绝对贫困的思路制定的。但是这一创举,冲破了按 “生活必需品”制定救助标准的禁锢。
此后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各国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得很快,所以救助标准中 “绝对”
的成分就越来越少了,制定救助标准的参照物逐渐转向名副其实的社会平均水平。
以上的历史过程说明,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和进
步,贫困定义也必然从相对保守、狭隘和封闭的绝对主义走向相对开放、发散和包容的相
对主义。对于贫困和反贫困的讨论,无论其出发点是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但逐渐地都
会殊途同归,并且在某个关键时刻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新的境界。
三、相对主义何以盘活了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关于贫困的讨论再次升华,已经超越了以往限于 “绝对贫困 VS 相对贫
困”的狭小范围,跃升为更加开放的 “多维贫困”。如前所说,现在常常讨论的政策理
念,包括阿玛蒂亚·森提出的 “可行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 “发展权利”,欧
共体委员会提出的 “社会排斥”,托马斯·戴伊 ( Thomas Dye)提出的 “阶层地位”,奥
斯卡·刘易斯 ( Oscar Lewis)提出的 “贫困文化”, 以及迈克尔·谢尔登提出的 “资产
〔 28〕
建设”, 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都与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生活行动和生活机会相关。
〔 29〕
如果能够将这些丰富多彩的政策理念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结构分化又功能耦合的大系
统,定能在彻底改变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上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效应。就这个意
义而言,多维贫困,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以以人为本为导向,对绝对主义进行扬弃后的更
加开放、更加发散、更加立体的相对贫困。
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以生活方式的视角来观察,很多从前被看作奢侈品的消费
品,如今都已经是生活必需品,而且 “几乎每家都有像电视机与洗衣机这样的消费品”。
“现在甚至那些最低收入的家庭也享有比 20 年前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但是,“与此同时,
在低收入家庭中,仍然广泛存在着营养不良、健康不佳、接受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机会有限
以及居住环境不安全等问题”。
〔 30〕
虽然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公开宣称的反贫困政策的目标还是 “基本消除绝
对贫困现象”。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的经验是城乡社会救助和农村脱贫攻坚并举。在消
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相对主义的因素其实一直都在不着痕迹、潜移默化地渗入。
首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机会的视角看中国
的救助标准和扶贫标准,其实一直都在不断调整。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始于上海,1993
年上海市实施这项制度时,确定的低保标准是月人均 120 元;而到 2019 年,已经是月人
均 1160 元,增幅为 9 倍多。就全国而言, 2006 年城市低保标准为月人均 170 元,到 2019
0 ·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