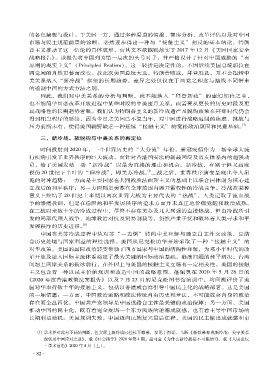Page 83 - 《党政研究》2021年第2期
P. 83
的各色猜想与设计。于美国一方,通过多种渠道的情报、智库分析、改革评估以及对中国
市场与民主规范前景的诊断,必然逐步得出一种与 “接触主义”相反的基本结论,特朗
普主义推动了这一结论的具体成形,而其文本依据则落实于 2017 年 12 月 《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该报告将中国列为第一层次的头号对手,并严格设计了针对中国威胁的 “有
原则的现实主义”( Principled Realism)。这一转折是决定性的,不因后续美国总统职位在
两党间的自然更替而改变。故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败选,拜登胜选,并不会扭转中
美关系落入 “新冷战”框架的长期趋势,差异之处仅仅在于两党之理念与路线不同带来
的遏制中国的方式方法之别。
因此,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分析与判断,就不能落入 “拜登新政”的虚幻期待之中,
也不能简单留恋改革开放进程中某些时段的中美蜜月关系,而需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及更
具战略性的长期趋势着眼。我们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新冷战遗产及脱钩政策在拜登时代仍会
得到相当程序的延续,因为今日之美国已不复当年,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焦虑、挑战与
压力前所未有,使得美国朝野缺乏一种延续 “接触主义”的宽松政治氛围和民意基础。
〔 7〕
三、新冷战、软脱钩与中美关系的再定位
时间投射到 2020 年,一个世界历史的 “大分流”年份。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全球大流
行疾病引发了世界秩序的巨大波动,而针对香港国安法的制裁回应及盟友体系内的超强动
员,给了美国发动一场 “新冷战”以最为直接的理由和机会。新冷战,有别于但又高度
模仿 20 世纪下半叶的 “旧冷战”,即美苏冷战。二战之后,世界秩序演变呈现出令人吊
①
诡的对冲趋势:一方面是主要国家在共同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建
立战后的和平秩序;另一方面则是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霸权性的冷战竞争。冷战在某种
意义上终结了 20 世纪上半期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主要代表的 “热战”,人类记取了流血战
争的惨痛教训,但是在稳固的和平发展秩序的追求方面并未真正地价值觉醒和政治成熟。
在二战以来数十年的冷战过程中,尽管不存在美苏及几大列强的直接热战,但由冷战所引
发的局部代理人战争、地缘政治对抗及贸易制裁等,仍然严重干扰和破坏着人类寻求和平
发展秩序的历史进程。
〔 8〕
中国在美苏冷战过程中从对苏 “一边倒”转向中美和解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结
合历史处境与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美国从尼克松访华开始采取了一种 “接触主义”的
对华政策,美国的国际政治转变带动了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结构性和解,为邓小平时代的改
革开放及融入国际主流体系奠定了最为关键的国际政治基础。港澳问题的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上两岸关系的破冰前行,在外因上与美国的接触主义立场有一定相关性。美国的接触
主义包含着一种以民主价值规训和改造中国的战略意图。蓬佩奥在 2020 年 5 月 28 日的
《 2020 年度香港政策法案报告》以及 7 月 23 日的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中,均回溯评价了美
国对华奉行数十年的接触主义,包括以香港或台湾引导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部署。这是美国
的一厢情愿:一方面,中国政治道路和政法传统自有历史和章法,不可能放弃自身的政治
存在而全盘西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道路自主性最关键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美国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既有着完全规训一个东方民族的道德成就感,也有着主导中国市场的
长期利益动机。美国规训失败,中国迈向民族复兴最后征程,美国的民主输出成就感和市
①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判断,但实际上新冷战已经拉开帷幕,参见于海洋、马跃 《新铁幕抑或新冷战:美中关系
现状及中国应对之道》,载 《社会科学》2020年第 4期;赵可金 《为什么新冷战是不可能的?》,载 《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20年 4月 (上)。
2 ·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