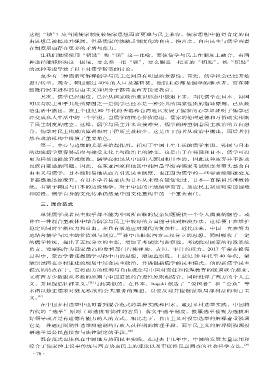Page 66 - 《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P. 66
这把 “锁”?应当说儒家制度较儒家思想而言更难与民主兼容。儒家思想中值得肯定的自
由思想已被提及并强调,但是儒家传统缺乏制度化的自由。换言之,自由民主与儒学两者
在制度层面存在更多的矛盾与张力。
让我们继续使用 “钥匙”和 “锁”这一比喻,要使儒学与民主在制度上融合,有两
种途径能够解决这一困境,要么换一把 “锁”,要么锻造一把新的 “钥匙”。换 “钥匙”
的这种考虑导致了以下对儒学转型的讨论。
至少有三种因素可解释儒学与民主之间具有明显的兼容性。首先,儒学社会已经开始
进行转型。现今,韩国超过 40%的人口是基督徒,他们未必都是儒学的继承者。而在韩
国推行民主进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曾在西方接受教育。
其次,儒学已经退位,已经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中撤退下来。当代儒学在日本、韩国
可以与民主和平共处的原因之一是儒学已经不是一种公共的国家性质的指导原则,已从政
治生活中撤出。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发展了儒家的心学即证明了儒学已
经变成私人生活中的一个学说。当儒学的核心价值隐退,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习俗确实帮助
了民主制度的建立。这样,儒学与民主并未直接冲突,儒学的转型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融
合。儒学对民主构成的障碍相对于伊斯兰教较少,这是由于前者从政治中撤出,而后者仍
然在政治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三,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开始起作用。相对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学来说,韩国与日本
的边缘儒学更容易适应与接受文化上与政治上的转变。这是由于在韩国和日本,儒学可以
更为轻易地被放弃或修改。儒学起初是从中国引入韩国和日本的,因此这种废弃并不涉及
民族自豪感的问题。因此,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中韩国最早废弃儒家考试制度并带头整合自
由主义与儒学。日本能轻易地从西方引进民主制度,也正因为儒学的一些要素能够被毫无
罪恶感地迅速废弃。有日本学者甚至认为日本从来没有被儒化过,日本一直保留其神教传
统。有别于韩国与日本的边缘儒学,对于中国的正统儒学而言,适应民主制度则更加困难
和缓慢。儒学自身的文化传承仍然是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一个重大责任。
三、混合范式
单凭儒学或者民主似乎都不能为中国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答。或
许在一种混合型政体中结合儒学与民主中较好的方面能寻找到解决办法,这样便于在维护
稳定的同时平衡权力和自由,并且有效地应对现代的复杂性。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
地结合儒学与民主的价值观与制度。 孙中山根据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同时吸收了一定
〔 25〕
的儒学传统,提出了五权分立的主张,增加了考试院与监察院。考试院对国家的行政系统
负责,监察院作为国家最高的监督部门行使弹劾、责问、审计的权力。2017 年蒙古修宪
过程中,蒙古学者还提倡学习孙中山的思想,增加监察院。上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梁
漱溟试图在乡村重建的规划中结合民主政治,并提倡新儒学的民主模式。他的新儒学民主
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将西方的权利与自由观念与中国对责任和伦理教育的强调联合起来,
又将西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与中国道德的合理性原则相结合,同时批评了西方的个人主
义,并且提倡社群主义。 与此类似的,在日本,Itagaki 创造了 “爱国者”和 “公众”等
〔 26〕
术语以修正儒家对毫无私欲的公共服务的理想,以便反对并控制谋取局部利益的利己主
义。
〔 27〕
在中国乡村选举中也可看到混合范式的某种实践和因素。通过乡村选举实践,中国将
古代的 “选举”原则 (即选拔有德性的官员)落实于选举制度。投票选举被视为选拔出
好领导或者是有道德有能力的人的方式。相比之下,自由主义对投票选举的解释着重强调
它是一种通过周期性选举测验制约行政人员任期的管理手段,而平民主义的解释则强调投
票选举是公民直接参与法律制定的手段。
〔 28〕
混合范式也体现在中国地方协商民主实践。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的发展大量运用和
综合了儒家绅士议事传统与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以及审议性民意调查的社会科学方法。
〔 29〕
6 ·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