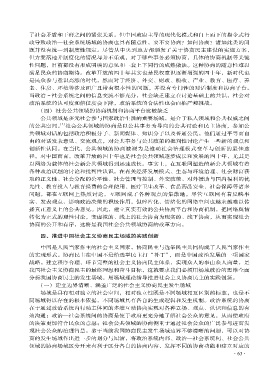Page 63 - 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P. 63
了社会矛盾和干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中国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自上而下的指令式行
政导致政治—社会系统场域的协商也具有随意性,要不要协商?如何协商?诸如此类的问
题并没有统一到制度性规定。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颁发了关于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方案,
但方案落地并制度化的情况却并不乐观,对于哪些事务必须协商,具体的协商机制等关键
性问题,目前都没有形成明确的意见和一套上下同行的成熟做法。这种协商的随意性难以
满足民众的协商期待。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其实也是民权意识逐渐增强的四十年,新时代也
是民众参与意识高涨的时代,然而对于经济、外交、财政、税收、产业、教育、医疗、养
老、住房、环境等涉及面广且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专门性的对话制度和协商平台。
当政治 -社会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不够充分,社会缺乏建立在讨论基础上的共识,社会对
政治系统的认可度和信任度会下降,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也会面临严峻挑战。
(四)社会公共领域的协商机制和协商平台比较缺乏
公共领域是多元社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场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
的公共空间。 社会公共领域的协商是以公共事务为导向的公共讨论和民主协商,参加公
〔 7〕
共领域对话的包括政治积极分子、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公民。他们通过平等而自
由的对话发表意见、交流观点,对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的批判性讨论产生一些新的观点和
创新性认同。在当代,公共领域的协商被视为是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变革与创新的最佳途
径。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社会公共领域逐步成长和发展的四十年,尤其是
以网络为载体的社会新公共领域得到迅速成长。事实上,在互联网塑造的新公共领域有着
各种政治议题的讨论和批判性认识。在有关经济发展模式、生态与环境治理、社会财富获
取的正义性、社会分配的公平性、社会管理与控制、外交政策、对外援助与国内福利的优
先性、教育投入与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医疗卫生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障等诸多
问题,都在互联网上热烈讨论,互联网成了各种观点的集散地。尽管互联网有着反映事
实、发表观点、影响政治决策的积极作用,但碎片化、情绪化的网络空间也越来越难以传
播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意见。因此,建立真实有效的公共协商平台和协商机制,把网络舆情
转化为正式的理性讨论,变虚拟的、线上的社会协商为现实的、线下协商,从而实现社会
协商的公开和有序,这将是我国社会公共领域协商的改革方向。
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场域的实践创新
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共同构成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实现形式。协商民主在中国不是给选举民主打 “补丁”,而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国家
战略。建立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实现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是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最终理想和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场域政治的思维全面
分析我国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用场域理论指导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
(一)建立边界清晰、涵盖广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生场域
场域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
同场域得以存在的根本依据,不同场域具有各自的生成逻辑和发生机制。政治系统的协商
在于通过政治系统内行动主体间的多维互动协商实现对各种立场、观点、认识和信息的有
效沟通;政治—社会系统间的协商是便于政府更充分地了解社会公众的意见,从而使政府
的决策更加符合民众的意愿;社会公共领域的协商侧重于通过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进而发
现社会公众的治理智慧。鉴于当前我国协商民主发生场域边界不够清晰的问题,可以对协
商的发生场域作出进一步的划分与厘清,将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社会系统间、社会公共
领域的协商场域区分开来有利于区分各自的协商内容、发挥不同的协商功能和建立对应的
3 ·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