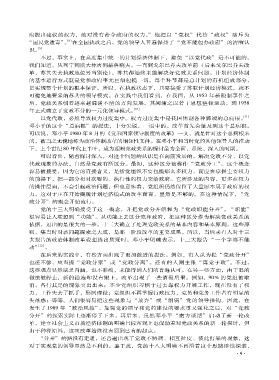Page 9 - 党政研究2019年第4期
P. 9
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他把以 “党权”代替 “政权”痛斥为
“国民党遗毒”。 在全国执政之后,党的领导人普遍保持了 “党不能包办政府”的清醒认
〔 8〕
识。
〔 9〕
不过,事实上,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避免 “以党代政”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赫鲁晓夫,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 (后来戈尔巴乔夫改
革、苏共失去执政地位另当别论),苏共都始终未能解决好党政关系问题。计划经济体制
的基本运行方式就是党和政府事无巨细包揽一切。每个环节都是总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实现整个计划的根本保证。所以,在执政状态下,只要接受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就不
可避免地要采纳苏共的领导模式。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在我国,从 1953 年新税制事件之
后,党政关系朝着越来越混淆不清的方向发展。其间辅之以若干思想整顿运动,到 1958
年正式确立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模式。
〔 10〕
以党代政,必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权力过度集中是我国体制各种弊端的总病根。
〔 11〕
邓小平的这个 “总病根”的提法,十分尖锐,一语中的。改革首先会触及到这个总病根。
可以说,邓小平 1980 年 8 月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是针对这个总病根来
的,被当之无愧地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邓小平和当时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推动
下,上个世纪 80 年代上半叶,成为理顺党政关系的探讨最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时期。
可以看出,随着探讨深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在向前发展的。解决党政不分、以党
代政现象的办法,自然是党政有所区分。最初,这种区分被称作 “党政分工”。这个概念
容易被接受,因为它的直接含义,是指党组织不要包揽那么多权力,而应在掌握主要权力
的前提下,把一部分相对次要的、执行性的权力交给政府。它所涉及的内容,更多在权力
的操作层面,不会引起政治问题,但也意味着,党组织仍然保留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的权
力。这对于正在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模式的改革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党
政分开”的概念开始流行。
党的十三大明确接受了这一概念,并把党政分开解释为 “党政职能分开”。 “职能”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功能”。从功能上去区分党和政府,把这种区分作为解决党政关系的
依据,迈出的是很大的一步。十三大确立了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这些原
则,集当时对该问题探索之大成,是那一阶段改革的重要成果。所以,当后来有人对十三
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提出质疑时,邓小平明确表示,十三大报告 “一个字都不能
动” 。
〔 12〕
在后来的实践中,有些方面出现了更加激进的提法。例如,有人认为提 “党政分开”
也还不够,应当提 “党政分家”或 “党政分离”。还有的人则主张 “寓党于政”。不过,
这些观点显然缺乏内涵,也不准确,未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在另一些方面,由于旧的
做法被停止,新的措施却没有跟上,改革出现了一些消极后果。例如,90%的党组被取
消,各行其是的现象突出出来;不少党组织习惯于过去靠权力开展工作,现在没有了权
力,工作失去了抓手,形同虚设;党组织不再掌握行政权力,党员和党务工作者有明显的
失落感;等等。人们很容易把这些现象与 “放弃”或 “削弱”党的领导挂钩。因此,在
发生了 1989 年 “政治风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要求重又强化之后,对 “党政
分开”的探索实际上逐渐停了下来。再后来,虽然邓小平 “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改
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客观上也促动着对党政关系的新一轮探讨,但
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改革始终没有回到已有的起点。
“分开”的路没有走通,还普遍出现了党政不协调、相互扯皮、彼此打架的现象,这
对于实现党的领导显然是不利的。鉴于此,党的十八大明确不再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探索,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