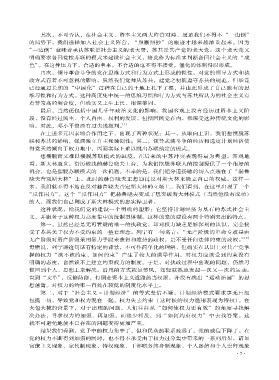Page 7 - 党政研究2019年第4期
P. 7
其次,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逼迫我们不得不 “一边倒”
的局势下,我们选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照搬照抄”的痕迹才越来越浓重起来。因为
“一边倒”意味着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共是共产党的老大党。这个老大党又
明确要求各国党按苏联的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将此作为标准来判断各国社会主义的 “成
色”。在这种压力下,合适的拿来,不合适的也不得不接受,僵化的体制得以形成。
再次,领导革命斗争的党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形成的惯性,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
政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我们党师从苏共,建党之初就遵守苏共的规范,但毕竟
已经通过长期的 “中国化”过程在自己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思
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与苏共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有
着非常高的契合度,但确实又土生土长、根深蒂固。
最后,当然还包括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客观上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
段,没有经过民主、个人自由、权利的发展。包括国民党在内,都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
响。对此,邓小平曾经有过尖锐批判。
〔 1〕
在上述多元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出现了两种状况:其一,从取向上讲,我们想摆脱苏
联和苏共的影响,强调独立自主和独创性;其二,领导武装斗争的经历和选定计划经济使
得党天然倾向于权力集中,因而实际上难以跳出苏联给定的模式。
想摆脱而又难以摆脱苏联模式的困境,在后来的中苏冲突表现得最为典型。客观地
看,斯大林逝世,资历较浅的赫鲁晓夫上台,为我们摆脱苏联人的控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机会,也是摆脱苏联模式的一次机遇。不幸的是,我们把分道扬镳的切入点选在了 “赫鲁
晓夫背叛斯大林”上。此时的赫鲁晓夫正想通过反对斯大林来确立自己的权威。这样一
来,我们就不得不站在反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立场上。我们看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
“反作用力”,这个 “反作用力”把赫鲁晓夫变成了想突破斯大林模式 (当然他没有成功)
的人,而我们自己则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忠实捍卫者。
这种状况,给我们党的建设一个明确的塑形:它坚持计划经济为基石的苏式社会主
义,并服务于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统制型体制。这样的党的建设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
第一,虽然已经是无可置疑的唯一的执政党,却对权力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完全接
受了苏共关于权力不受约束的一整套理念。列宁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 2〕
毋庸说,列宁讲这句话有特定的背景,不可作简单化的理解,但确实在认识上对共产党掌
握的权力 “该不该约束、如何约束”产生了较大的误导作用。对权力应该受到约束没有
明确的态度,自然谈不上建立约束权力的制度。于是,对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仍然习
惯回到个人、思想上来解决。沿用的方式就是整风,驾轻就熟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运动。
直到 “文革”,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跳出 “运动治国”的思
想藩篱。对权力的约束一直处在较低的制度化水平上。
第二,对于 “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的等式坚信不疑。计划经济模式要求事无巨细
包揽一切,导致党和权力混在一起,权力失去约束 (这时候的权力滥用表现为特权)。在
大包大揽的背景下,对于出现的问题,人们往往从 “如何使权力更有效”的角度寻找解
决办法,寻求权力的加强、再加强,而很少相反,到 “如何约束权力”中去找答案。这
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已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结果我们看到,党手中的权力集中了,但和民众的联系疏远了,党的威信下降了。在
党的权力不断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诸如
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现象、特权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现象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