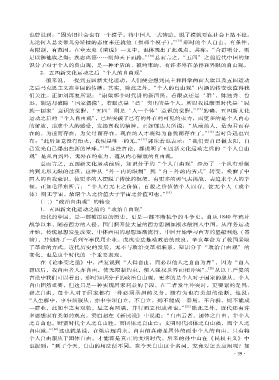Page 39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P. 39
也曾说到:“因为旧社会也有一个模子。将中国人一式铸造,脱了模就要在社会上站不稳。
无论何人总要带几分矫揉的态度来迁就他 (指那个模子)。” 那时的个人自由,有条件,
〔 13〕
有限制,有范围。在章太炎 《菌说》一文中,也体现出了此观点,其称:“合群明分,则
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 总而言之,“五四”之前近代中国的知
〔 14〕
识分子对于个人的自由观,是一种矛盾的、被约束的、有许多外在条件和界限的自由观。
2.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个人的自由观”
一般来说,一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便会想到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及五四运动
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除此之外,“个人的自由观”内涵的转变也值得我
们关注。正如刘再复所说:“康梁那个时代讲的新国民,着眼点还是 ‘群’,陈独秀、鲁
迅、胡适却破除 ‘国家偶像’,着眼点是 ‘己’突出的是个人。所以我说康梁时代是 ‘民
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五四’则是 ‘人—个体’意识的觉醒。” 的确,五四新文化
〔 15〕
运动之后的 “个人自由观”,已经突破了已有的外在的可见约束力,而更多的是个人内心
的解放,追求个人的感受,发扬真我的精神。正如郁达夫所说:“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
在的,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当时鲁迅也宣
〔 16〕
布:“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郭沫若也表示:“我们要自己做太阳,自
〔 17〕
己发光自己爆出些新的星球。” 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 “个人自由
〔 18〕
观”是从内到外,无外在约束力,遵从内心解放的自由观。
总而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的 “个人自由观”经历了一个从有形制
约到无形无限的过程,这种从 “外 -内的限制”到 “内 -外的内省式”转变,唤醒了中
国人的自我意识,使更多的人摆脱了传统的框架,有更多的勇气去挑战,去追求个人的幸
福。正如毛泽东所言: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 (或个
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 〔 19〕
(三)“政治自由观”的转变
1.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 “政治自由观”
近代的中国,是一部被压迫的历史,更是一部不断抗争的斗争史。自从 1840 年鸦片
战争以来,随着西方的入侵,国门洞开使大量的西方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从洋务运动
开始,传统思想发生改变,中体西用的思想逐渐流行,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 (器
物),并创办了一系列军事民用企业。戊戌变法推动政治的改良,辛亥革命为了救国采取
了革命的方式。近代历史的发展,无不与政治变革相联系,知识分子 “政治自由观”的
变化,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 《论事变之亟》中,严复说到 “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因为 “自入
群以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 从以上严复的
〔 20〕
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自由观,更多的是个人对于国家的服从,个人
自由固然重要,但这只是一种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更要紧的是国、
群之自由,每个人对于国家都有一种必须承担的义务。康有为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说:
“人生群中,事事须服从,亦事事须自立,不自立,则不能成一器用,不合群,则不能成
一群业,此如车之有双轮,屋之有两墙,并行而立相成者也。” 除此之外,近代还有许
〔 21〕
多思想家有类似的观点。梁启超在 《新民说》中说道:“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
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
自由减。” 这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自由的真谛是团体的而非个人的自由,只有将
〔 22〕
个人自由服从于团体自由,才能算是真正的文明时代。后来的孙中山在 《民权主义》中
也提到:“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应用呢?如
9 · ·
3